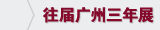博物馆的实验性:从贡布里希中国化谈起《美术文献》
艺术理论的全部尴尬大概就在这里了,我们能够清楚地阐述杜尚把现成的小便池变成艺术品这一事件吗?但是,阐述这一事件又成为20 世纪艺术理论发展的起点,是理解现代主义艺术所绕不过去的话题。贡布里希基于其经验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类事件上绝对不会玩概念游戏,所以只能小心谨慎,避免解释,而只以描述为表达方式。所有描述中,看来只有“实验”一词最具中性,也最有弹性,所以,贡布里希用“实验性艺术”来概括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只是,贡布里希到了中国以后,在“贡派”的理论策略中,“实验”被端上了艺术现场这张饭桌桌面,变成了秀色可餐的理论盛宴。然后,大家起劲地吃着嚼着,最后居然嚼出了“本土”的滋味,从而上升为一个严肃的理论术语,再然后,又在某时某刻因某种不言自明的原因而进入了主流,进入高等美术教育在编目录,从而完成了“实验”这一个术语升华的漫长历险。今天,“实验艺术”已经成为高等艺术教育的普遍事实,但关于这一术语的历险过程仍然鲜为人知,尤其是,发生在这一术语背后的理论分野更没有太多人关心。本来,站在贡布里希的立场上,我们完全应该认同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判断,这一判断并没有多少好话,贡布里希只是欣赏其中的创新性,却无法认同其核心价值。一旦离开贡布里希的立场,我们才会发现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学术转向的意义所在。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只有坚定地站在区域、民族、阶级与资本这一系列批判性的社会基础上,艺术才有可能离开中性的“实验”而有所归依。今天不是古典主义在召唤我们,而是发生在全球化当中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重大利益冲突在警醒我们,这才是关键的事实,艺术无法、也不应该离开这一事实,而不管它是否“实验”。
五
既然实验艺术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关键词成为描述不管是学院还是社会那些试图突破原有的写实主义框架的多元努力,则这一努力也必然体现在博物馆中,而让博物馆的展示也开始具有了某种实验性。现在看来,对博物馆来说,其实验性最大的呈现就是打破展墙的平面化处置,把观众从过去那种怀着迷恋般的崇敬徜徉在一幅又一幅杰出作品面前解放来,让博物馆的空间变得复杂与多样,变得不再那么平面,甚至基本上不再平面化。从广东美术馆前几届的三年展的展示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变化。显然,这一变化是一个进行时,应合着实验艺术的正规化与主流化。只是,如此一来,博物馆传统的功能,也就是本文开始所提出的贡布里希的“四功能”看法,可能就要发生变异。博物馆不再仔细定义“收藏、研究、展示和公共教育”之间的作用,在实验的冲击下,已经出现了不能收藏,至少是不能简单收藏的作品,也出现了违背通常展示方式的作品,其主题很有可能是颠覆展示本身的一种短暂的视觉存在。既然有这样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