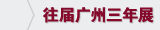直击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布展现场《雅昌艺术网》
作为他者来再现的。可见,不是“再现”与意识形态有关,而是“再现”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大众之成为大众,是精英权力集团与大众对立之间建构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与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不断把文化领域划分为“大众”和“非大众”的①。这种权力集由一种相对统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经济的、道德的、美学的、教育的—联合组成,如美术院校这类的教育系统、美术馆这样的艺术机构就发挥了把“有价值的艺术”与部分“无价值艺术”区分出来的作用。由此即可见出,大众文化的“大众”,尽管在构成比例上是社会的最大群体或基本构成,而权力/ 知识精英倒是一小撮,但大众无法再现自己。所以,有关大众生活的一切包括大众艺术长期被统治文化打入另册,成为主流之外的边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依托于人类学、心理学学科的发展,大众的生活和行为成为后现代文化学者的研究对象,阶级、性别、种族成为热议的话题,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词被认为是“再现”或“错误再现”。如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发掘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并非作为真实历史的存在的东方可靠代表,而是欧洲东方主义者想象的或构造的空间,是一种知识编码和制造,意在以文化上的‘它者’来陪衬自己的优越。”如此,一些思想家和文化学者试图重新“再现”“大众”自身。如约翰·费斯克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就坚决反对视大众为一群没有鉴别能力,经济上、政治上受工业巨头牵制的被动的、无助的乌合之众的观点,“我们有必要把人民想成一个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一大批以各种方式遵从或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只要“人民”这个词还有用,就应把它看作一个不断变动的和相对短暂的构成体组成的联盟。它不是一个一元的,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处于重新构造之中的术语,与统治阶级处于辩证关系之中。”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形成三重定义:第一是商业化市场性意义上的,把大众文化视为完全受操场控的被动力量,如法兰克福学派。或者相反地用一种完整的可替代性的真正的大众文化与商业文化对立。第二种是描述性的,认为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做的一切事情,这种概念无法理解大众是如何与精英或主导的对立中建构出来。第三种是与精英或主导的对立中建构出来,其形式和活动以特定阶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体现在大众传统和实践之中。最关键的是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之所以重视“大众文化”,是因为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企图利用大众文化来控制接受者对意义的快感的生产,另一方面接受者又可以利用这种资源来生产颠覆和抵抗的效果。
在这种语境下,一些当代艺术家开始与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合谋,加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艺术媒介的多元化,影像、装置、行为等逐渐解构了架上艺术的精英化态势,艺术与艺术创作本身遭遇了本体性诘难,从而不得不面临其是不是艺术的问题。更多的当代艺术,与其说是一件艺术作品,毋宁说是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也就是说,艺术目的不在“艺术”,而是已经被“非艺术”化了。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作者之亡”(The Death of Author),观看者面对一件当代艺术作品,第一感觉已不是艺术的本体而是社会学、人类学或政治学范畴的东西,关于它的价值判断不再以艺术语言为准则,而是以它的社会指涉深度或政治意涵的程度来认定。如此,关于作品的阐释便获得了空前的重要性,以至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