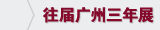第四届广州三年展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录音整理)
1.《南方都市报》:你好,我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我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罗一平馆长,因为这一届广州三年展持续时间这么久,应该是很少见的,可能不止是三年展这个名称。那么我就想请问罗馆长,为什么决定做一个跨度时间这么久的一个三年展?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张旭东教授,因为您刚才提到80年代美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之间比较深入的互动关系,那您觉得造成像今天这种彼此之间不过问的这样一个局面,最大的壁垒是在哪里?我第三个问题是请请教一下姜节泓先生,因为您刚才也提出说双年展、三年展不仅仅是美术馆的事情,也是一个城市的事情,那么您在策划这个主题展的时候,与广州这座城市之间的互动有在展览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谢谢!
罗一平:我来回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三年展要跨度跨3年。这里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因为今年是三年展是我们设定的从第三届三年展到第四届三年展刚好第3年。今年按常规来说,是必须要做第四届三年展的。那么当去年的改扩建工程纳入计划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今年10月份改扩建工程就开始。所以我们想三年展要么在改扩建工程之前做,要么在改扩建工程之后做,那就横跨了6个年头。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下,三年展是要如期进行的,把三年展和改扩建的工程放在一起延续做3年,把整个美术馆的改扩建做成一个艺术的展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思路。可是由于后面种种的原因,包括我们的报批计划等等,使我们在今年广东美术馆的改扩建还没进行时就作了一个调整,即把第四届三年展做成一个动态的展览,做成一个能够突破展览开始、不停地滚动、深入地探讨研究审理问题的一个展览,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突破原有的展览,到展览结束以后,它的理论探讨、它的整个思考就着它展览的谢幕而结束。我们恰恰是就整个展览的开始滚动过去,用3个跨年度的时间把这个展览提出的议题反复地来思考,反复地来论证,反复地来讨论,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具有一个纵深文化的展览模式。
张旭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最直接地回答大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因为钱、因为市场、因为专业化,大家都是为各个不同的自己顾客、自己的老板、自己的体制、自己的专业的路径在忙,大家在一起忙就没有时间在一起讨论,就没有时间在一起关心共同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专业化。当然这个问题不完全是负面的,任何一个方向,艺术也好,学术也好,技术也好,你要做得好,肯定是要有一个专业化的过程。跟80年代相比,80年代现在想,其实很多人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很业余,确实是这样。但是业余中,我们就一个概念叫伟大的业余者,这些人往往是最热爱艺术、最热爱思想、最热爱学术的。当时人也比较少,氛围比较集中,一个宿舍就可以包括学经济的、学哲学的、学美学的,晚上一起关灯就可以在一起讨论。那么像今天这样的情景、场景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所以就需要像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平台把大家重新聚合到一起。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有方向感的,是有一个总体价值的。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虽然也是提得很明确,但是那时候中国前30年的价值的构架、框架还在,但是另一方面一下子全世界打开大门,新旧交叠,有一个交叠的重合部分,我觉得80年代是一个外面是一个今天看来已经负面的东西,在当时还是被国家体制(今天看来从另一个层面看比较僵硬地国家体制)挡在外面,但事实上是一个保护。就是说我们第五代电影,如果那时候好莱坞大片都可以进来的,它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资源进行这样的探索。我想艺术界、思想界都是讲全世界的。事实上,一个强势的国家奠定了一个价值的基础,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而这个东西被逐渐打掉以后,在我们理想中的所谓的市场或者某个空间里面要建立起新的思想上的热烈,其实是持续的问题,它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面对着各种更强大的、更持久的这种话语、话语权的、价值体系的压力。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化生产、思想状态是一个非常破碎非常不成型的状态。当然不可能简单地回到80年代那个状态,也不可能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在今天这个境遇下思考怎么能够恢复自身问题的意识和价值的整体性。这是我想也是学术界的朋友都热心参加广三展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