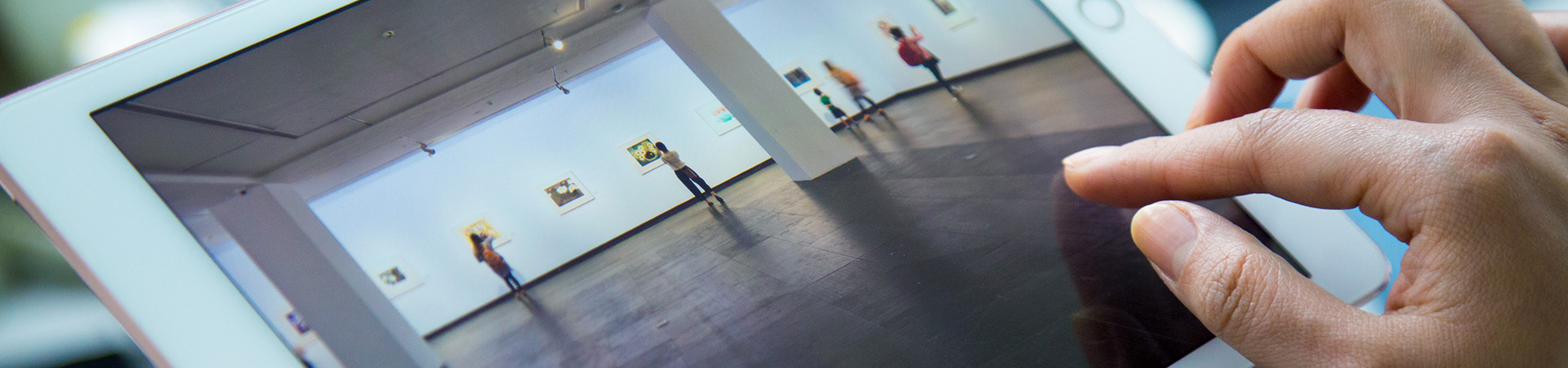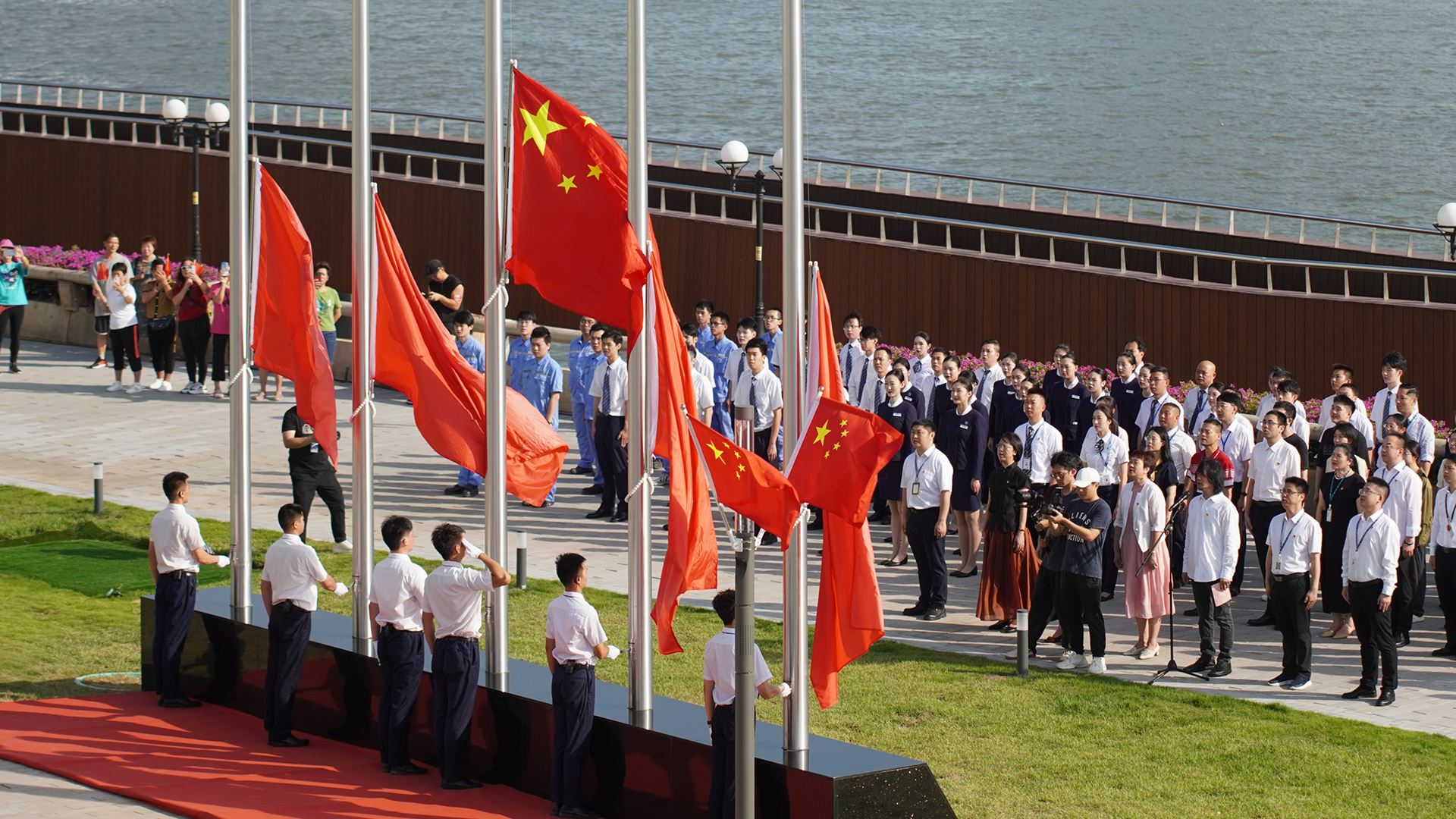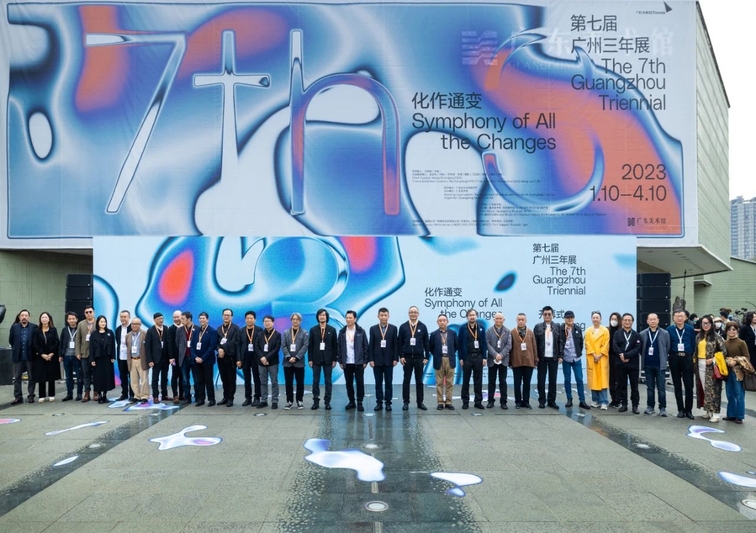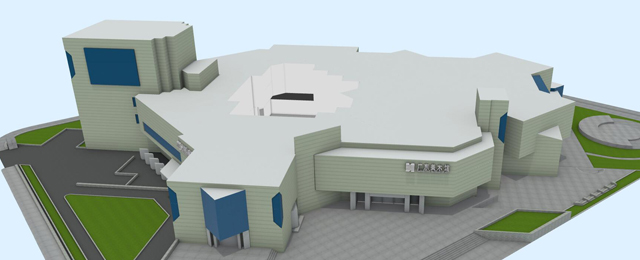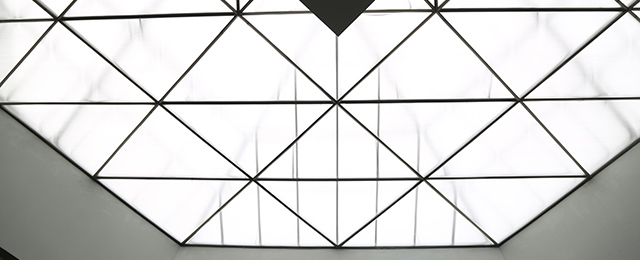对话丁乙:在绘画中寻找新的时代精神
录入时间: 2018-09-19
采访及撰文 | 贺婧
时间 | 2018年6月30日
地点 | 丁乙工作室
贺婧(简称“贺”):我们或许可以先从“观看”而不是作为结果的画面谈起。多年以来,您的作品无论经历了多少画面上的变化,一个不变的东西是它们都在致力于对一种“观看”的创建。这种观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要求观众不去预设任何联想或阐释的彼岸,而返回到观看本身。正如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那句“你看到的就是你在看的”(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那么对您来说,画家的作品和他的观看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丁乙(简称“丁”):在这个系统工作三十年,持续工作的时间很长、每天与画布打交道很近,也就是说,始终好像是沉浸在里面。对于这个过程,我觉得最容易解释的一个字就是“悟”——你总在想,这样沉浸在里面到底是要做什么?这么多年过来,最重要的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因为你是一个画家,你工作的重心是和画画打交道,那么无非就是要产生好的画。这种好的画可以说是用你的身体力行去沉浸、去表现、去揭示,同时这种感觉也通过你的画面传递给观众。一张画要怎么让观众看到的时候有惊喜,然后不断看的时候有更多的发现和感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画家要给你的绘画里面注入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是宏观把控,包括画面的结构、关联、气势、颜色等等;另一个就是细节,你不断地让观众去观看,他的目光在这样的画面上是不停移动的,这个移动其实是画面带给观众的,也就是说,画家赋予它每时每刻的变化。
当然所有这些都与我建立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就是没有一个完全的焦点、没有中心,它本身就是散点式的结构,没有巨大的纵深感;有的时候又是非常平的,它是散发、弥散在整个画面上的。在传统绘画中,观众的视觉是由艺术家引导到一个焦点上的,会忽略周边的其他东西,因而在焦点以外的地方就是“暗”的;而当你将这些焦点去掉,让画面“平面化”之后,其实每个地方都是焦点了,即使在那些“暗”的地方,实际上是有着相同的笔触、方法和结构。所以这是我的方法和古典绘画之间不一样的地方。
贺:80年代中期,您的绘画实践开始于对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和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笼罩下的艺术实践的“不信任”,是在这种双重“不信任”的基础上,您希望寻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完全个人化的思考和实践方式,包括确立了“让绘画不像绘画”的探索方向。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绘画道路是从一个具有否定性(而非继承性)的起点开始的?这个起点富有非常清晰的问题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您的创作并非是远离意识形态思考的,只不过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多是指一种绘画的观念性立场而不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
丁:关于这个问题侯瀚如曾经有过一句话:“丁乙也许是最意识形态的画家。” 实际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种现状,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系统都在寻找新的出口,艺术领域可能更敏感、动作更快一点。当时又正好是求学的时代,所以对未知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对于西方当代艺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全貌,了解的都是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所以就特别想了解。当时除了通过很有限的画片去了解,还有非常少的翻译过来的西方艺术史。有一本叫《西方现代艺术简史》,时间差不多覆盖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本东西很薄,基本上都是黑白图片,但是在1982年,通过这本书就能基本了解西方的一个系统。看过之后,你就会觉得西方在差不多这样一百年的历史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就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站在新的角度上起步,既能够和西方互补,又能够和中国以往认知的艺术系统有所不同。在学校做学生的那段时间,我能感受到我们接受的艺术教育系统与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既有中国的传统,又有前苏联的一些影响,所以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实际上在这之前,我的知识结构在私下里是在学习巴黎画派、印象派,几乎写生都在试用这些方法,为我打下了技巧的基础。所以当你用这些基础技术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当时的主流绘画,比如说上海美术展览馆还在做的大型主题性展览,你就会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懂技巧,同时开始不信任这个现状。以这些为基础,你就很快想建立起一些东西。而我自己当时在学校的学习是在国画系。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先生在教我们,年纪很大了,在社会上名气也很大,采用的还是很传统的师徒制方法,通过临摹来学习。而我下课之后一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就开始画试验性质的抽象作品。但那个时候实际是比较混乱的,有感而发什么都画,可能仅仅就是一本画册、一本书让你产生了画画的灵感。因为之前没有考取油画系,我反而决定去学习一些不了解的东西,就进入了国画系。但很明确,我也没有想要成为国画家。在1986到1990年的这四年学业期间,我从未停止过当代艺术的实践。
贺:那么您跟余友涵老师学习是什么时期?
丁:那个时候就是受到巴黎画派的启蒙,1980到1983年之间。余友涵那个时候在工艺美校做老师,但他实际上三年里面也只教过我们摄影课,都没有教过绘画。82年就有同学把我带到余老师那里,我带着一大卷作品,他就会指点一下。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终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做艺术家。所以虽然读的是装潢专业 ,业余时间全都在画画,包括周末。我一般一个月回上海(市区)一次,其他三个周末都安排自己画点东西。余友涵那个时候在学塞尚、学印象派,很多画我都是看着他画的,包括81、82年开始试验抽象。所以从学习西方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很同步的,可能中间的时间差就是两三年,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他的理解比我深刻地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否定了国内主流的方向。
贺:从您早期对于周遭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变化的摒除;到1998年您忽然意识到上海巨大的变化对您产生的影响,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荧光系列”的创作;再到近些年,我们看到您的创作实践似乎又回到了更多朝向绘画内部予以探索的道路上。这几次变化之间好像是存在着一种由内向外、再由外转向内的过程。您自己现在如何回看这样一个轨迹?如果说90年代末的社会变化让您意识到艺术家需要与他的外部世界发生关系,那么到了今天,您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吗?当您自己的体系已经完全建构起来并且越来越成熟,所谓的“内”或“外”的关系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丁:艺术家的创作历程,有时候是有意为之,有时候你又想摆脱这种策略性的东西。实际上我有过一段非常长的观念时期,很有策划性,好像要树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需要绝对和自治,摒弃任何情感成分,它变得严格、极简,或者说是绝对理性。因为在早期,你就是要确立自己的风格,就想让绘画有意为之,保持住这样一种统一性。而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你会发现这样绝对性的东西并不能涵盖自己全部的绘画历程,必须有新的角度、新的看法,随着年龄增长也会有新的经验,让你的作品在三十年的历程里产生很多变化和枝节。所以在荧光系列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巨大的变迁刺激了我的创作,对于城市化的看法被纳入到我的抽象系统里。这个过程的确让我的绘画产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到今天仍然有,只不过它的性质可能已经有所改变。
近几年,我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很难定义。我隐约觉得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精神,这种精神跟整个社会巨大的转型有关,这种转型让你能够以更高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98年的时候,你只是以中国为视野,你只看到你自己的世界;而这几年我希望能将自我的世界、中国的世界真正放在国际视野里去看待,这个视野有点难以表述,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有点复杂。 近几年我旅行最多的地区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这些地区以前是不了解的。以前我们关注的都是发达国家、主流艺术世界,这些东西放到今天仍然重要,但你的视野应该更大。这些旅行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对于这些国家的不同文化给了我很大的补充和感触,原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了解。
另外一个是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力量在第三世界扩张地非常厉害。制造业已经是中国的主流,而相比之下,艺术、文化仍然不是。你如何承担这个东西呢?当你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有主导性的同时,文化上是否能具有真正意义的主导性呢?我们的文化还是很弱的,缺少文化自信,也没有真正具有全球性认知的价值观,能够去拓展新的文化体。所有这些,都让我思考在绘画中你要追求什么,全球化的语言和价值观在哪里,这个很复杂。比如说,“一带一路”主要就是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经济扩张,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但缺少文化的先导。所以我觉得文化在今天变得尤其重要,需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思想不强,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发力。但是作为一个画家,很难有办法去改变整个局面,我只能感受到这种可能性,让它在创作之中有所呈现。可能目前我在探索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希望在作品中能有一种能量的爆发,同时又是使用很中性、抽象的符号,但是可能能够把这个时代的某种雄心保留下来。
贺:侯瀚如曾经说过,您作为个人主义艺术家的可能性,是在上海这个城市才得以成型;也有画廊家认为,“丁乙的画作只可能诞生在上海”。您自己认同这个观点吗?
丁:从个人感情上,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我终生居住在上海,也从没有意愿离开上海,这些可能是缘于我对上海的熟悉、对这个城市生活的满意。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很多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上海。对于这个城市的变化,每一次的转折我都能感受到。我不知道侯瀚如的评价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是从我日常的工作来说,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上海能让你感觉到最喧嚣的、最繁荣的大都市气息,而你进入工作室的时候,你可能又是被社会遗忘的。它使我既能保持独立性,又能与世界相通。
贺:谈到城市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联系,您的创作反而让我更多想到上海这个城市与中国早期的工艺美术传统、设计之间的亲密关系。您似乎从来不排斥“工艺性”这个被很多画家、前卫艺术家所忌讳的问题,您个人也有过从事设计工作的经验。那么,这种与工艺、设计,与现代都市紧密关联的基因,对您而言更多是来源于个人化的东西还是来源于上海的都市传统和环境本身?
丁:跟上海的环境和我个人经历都有关系。上海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亚洲最繁荣的城市,这种繁荣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城市时尚的理念,这个理念与当时的巴黎、纽约、东京都是一体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你对审美的追求是带有时尚化的,也就是说,你对所使用的物品、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带有品质的要求。所以为什么有所谓上海是中国最洋派城市的说法?因为它最接近于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反观80年代,中国很多城市都不太像城市,有点像农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与现代都市是直接相关的。当然,当代艺术的命题除了关注人性、精神层面,还有一些形式的东西,这些东西与都市文化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上海,好像从出生以来,周围的环境就会让你投射到一个国际视野里面,这造成了在很大层面上,你都不会去跟国内做什么比较,比如你的创作就根本没想到要去参加北京的展览,而是去参加纽约的、伦敦的展览。这种意识很可能从你的前辈一代开始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它可能是非常潜在的。
贺:您的创作最为清晰的一个特征在于一种重复的节奏感,当然这种重复不是原地复制,而是在重复中生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一方面这种重复迫使整个绘画系统发生了一种均质化的样态,也就是汪民安老师曾经提到的“一张画是另一张画的共振”;而同时间,重复的不断发生就促成了演进。就像是一种微观上的静态最终引发了宏观层面的动态,从不变中生成了变化。这种绘画行为本身富有很强的观念性。那么对您而言,这样一个经年重复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绘画行为,是否比最终的画面本身更重要?
丁:有时候我一天画下来,感觉自己这个方式很像传统的画家,虽然脑子在转,但行为方式很传统,花大量时间融在创作里面。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我的灵感之源就是这些工作本身。每一张作品的变化都是跟前一张未能完成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当完成了一张画之后,就会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当一张画没有完成的时候,它也会生成对下一张画的作用。比如《十示 2018-1》,画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忽然觉得这张画的场景很像我去年在敦煌看到的雅丹地貌——它实际上就是几百年的风沙把一些自然的山侵蚀掉。那么我就觉得类似这样的一张画,应该再画一张更大的,场景上更丰富的。同时,这张画在图形上也有一个突破——原来更多是在平面中隆起的,而在这一张中就产生了希望它有一种斜向冲击力的想法。而当更大的这张画《十示2018-2》完成之后,我就开始想,用什么方式来改变它的基底的东西,于是在下一张中,就开始对色彩进行重新配置,而为了让这个配置更为清晰,你又觉得这里的色彩必须是一个淡色调的…… 就是这样,产生了一种画与画之间相互作用、推衍的过程。
贺:所以说是从这个推衍的过程产生了画面本身?
丁:是的。创作的变化和演进,这个演进可能包括在材料的寻找上、色彩的配置上、技巧的变化上。但不变的是一张到下一张,一张未完的问题再到下一张的问题,真的是推衍的过程,三十年都是以这样推衍的方式在创作。
贺:您曾经说过,希望“绘画仅仅回到形式的本质,形式即精神”。在“十”字形这个构成您几乎所有画面的最基本的元部件上,似乎看到了这句话的印证。您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使“十”字丧失了它的符号性,即切除了它的所指,使它仅仅成为了一个形状、一个构成画面的纯粹的形式,而这个元部件的繁殖、变化和推衍构建了您的创作系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绘画从最初的起点开始就是“极简主义”的,它同时呼应了(前面所提到的)观看机制层面的“极简”。或者说,无论最终的画面如何呈现出一种色彩丰富和形状的“繁多”,您的作品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始终都是极简主义的。
丁:起步的时候跟今天比,从表面来看更极简。当时的方向很明确,要极简,更平面,因为极简无非是形状的最简单化,还有一个是画面的绝对平面性、色彩的最低限度,无非是这几条。那么我自己还是把自己定位在极简主义的艺术家里,但是这种极简与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极简,或者是之后斯特拉这些六七十年代的极简,已经是不一样了。
比如说马列维奇在一百年前的时候已经做到了真正的极简,就等于说这个门被他封死了,黑上之黑、白上之白,已经完全没有余地了。而我所说的极简,是如何在最低限度中达到绘画性的调配。比如色彩,我用荧光色创作了十二年,它的整个色系差不多只有四到五种颜色,十二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极简的色系里工作;另外所使用的符号,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元,十字或者米字,据此工作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极简。
贺:您一直在强调关于精确性的问题,它代表了绘画理性通道的产物。在早期,您借助尺、鸭嘴笔这些工具来寻找这种精确的概念;而近年来,精确性在您的绘画中表现为一种推衍的成像方式、一种元语言(“+”和“x”)的综合算法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认为您的作品与传统概念上的“抽象绘画”是存在距离的,前者更多是在以形式和色彩的表现来生成对描绘性、叙述性的反抗,而您近年来的作品不仅仅是基于形式和色彩的,它存在着一种更富有当代成像机制的基因。
丁:我也一直在反思,今天的当代艺术、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它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图像学的角度,需要有一种“新”的图像,抽象艺术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去分析中国前三十多年的当代艺术实践,你会发现在图像学上出现了问题,那种图像学的指向性是短暂的,它只是社会某种小情绪,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反应,所以它所产生的图像缺乏永恒的价值。在抽象领域里,因为抽象图像本身不太直接对应于社会现实,所以自由度更加宽广。某种程度上来说,抽象艺术是最容易“上手”的,但也是最难的艺术。从最初开始我们能看到两种抽象:理性的,或者感性的。感性的抽象,因为它是抒发性的,任何人都有抒发的理由,都有抒发的能量,他可以一挥而就,但持续性是最大的挑战,这种持续是不是可控的?让自己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画里,这不是一时的状态可以把控的。所以有时候在国内很多抽象艺术的群展上,我们会看到边上的作品让你感到从图像学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旧的图像、以前的图像,它自身缺乏挑战性,这是从时间上来说;有时候还会有诸如纽约的抽象、亚洲的抽象这样的说法,这里还有了地域性。抽象绘画的领域里往往就会有这些东西。而对我来说,一种新的、这个时代的图像,一种能够体现我自身独特表现方式的图像,才是我最最在意的东西。
贺:谈到工艺性,您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组看似矛盾的东西:一是求于认知层面、直达图像之物性探讨与语言结构的绘画;而另一个则是来自工艺美术传统、孜孜耕耘于纯粹技术层面的制图之术。这是两个看似难以相接的端口,是如何在您的作品中同时存在并且达到互通的?
丁:我自己是很迷恋这种矛盾性的。我对绘画的评判原则,一个是“正”。一张画一定要“堂堂正正”,不要耍小聪明,不要做手脚,甚至是做肌理,去埋设什么东西,必须是非常正气的、正向的这样一种状态。包括创作中的时间性因素(不要有速成的心态),都是保持所谓“正”的一种主要配置;第二个,在“正”的前提下,我一直希望作品“不顺”。它不是要流畅、顺畅,或者好看、优美,这些东西我是否定的。要很不顺的,里面有一些骨头。是这些东西让一件作品在“正”的前提下会有些“歪”,有点怪,在设计里面有种东西,设计与绘画结合可以调配这种不顺,你看绘画也不像,设计也不像,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
另外绘画不能指向性太明显了,它需要有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也许是模棱两可。艺术家有时候用语言很难完全阐释清楚,但是他的图像是能让观众有所感受的,而观众的感受可能也是模棱两可的,也不能像数学那样明确,有绝对的答案。
贺:所以您认为工艺性,或者这种带有技艺层面的东西,其实是在帮您调配“正”与“不顺”之间的关系?
丁:是的。但是同时这些年来,所谓我的风格,就是由这几个因素组成:第一是格子,整个画面做了格子;第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线来表述的;第三,“+”字或“米”字符号。这三个东西构成了我的风格,区别于其他艺术家。其他的都是历程的变化,而这三个东西代表了我创作的基本面貌。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带着设计性的,所以从创作之初,这个设计性就跟随着我,一下三十年。
贺:作为一位画家,身体与您的作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显然在您的系统中,身体既不像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那么富有存在感,同时,观念和技术上的理性设置也无法完全抛弃身体的介入。比起那些表现性的、激情洋溢的画家,“身体”问题在一位常年重复着相似的绘画动作的画家那里似乎要复杂得多。
丁:是的,更复杂、更内在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动作是外化的,是可以表演的,动作的起伏可以更加富有节奏。但是实际上类似像我这样的作品,更多是一种身体的、持续的动态性工作。抽象表现主义之所以成为行动画派,是因为它的动作幅度很大,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它是腰的动作更多,我是手臂、或者说是手腕的动作更多。我想艺术不应该是由所谓的动作性来评判,不是说身体的某个部位动作幅度越大,它所产生的动能就越大。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微观”与“微微观”之间的微妙关系。动作的痕迹都在画面里,只不过我的作品更加微观。从工作状态来说,也许像这种微观的创作,它所产生的体力的持续性更强。因为你一工作就是10个小时,如果换成是波洛克可能已经完成三张画了。
最近这几年,我的工作状态特别好,特别想工作,而且停不下来,能让自己真的沉浸进去。在早期,也就是在1991年那段时间我有过一段这样的状态,我现在觉得这个状态又回来了。你能够有很完整的时间完全投入其中。91年那时候,我通常是下午开始工作,有时候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就骑自行车随便去看个什么电影,十点钟再回到工作室继续画,一直到早上四点。那个时候工作和生活完全在一起,所有生活都是围绕创作,这是最好的状态。我现在的状态和那时候差不多,所有时间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创作,然后累了午休半小时,但是你所有的精神状态、思想状态,所谓的时间的主要分布,都是围绕着创作,所以这真的是最好的状态。
贺:到今天为止,您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吗?我们知道您在很多年的实践中,反复试验了不同的材料、技法,包括对于绘画所作出的不同限制与开拓。而近几年我们看到,表面的、技术性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少了,您更多在针对“结构”本身在处理问题(而并不简单是“越来越抽象”的问题)。
丁:当然有,这个难题或者说是不断推衍的。一个是创作的状态,一般来说创作状态是有起伏、有峰值。近几年,这种峰值不太明显,当然我在靠一些外在的东西在“吊”着它,比如展览,每年一个大展览,让我调动所有的能量、激情、工作状态来进行工作。
每年给自己设定的展览里都有新的作品,这些新作品和上一年之间的变化,也是一种变化。同时并进的是,除了图像的变化,还要有更深层东西的思考在进展着,包括视野的变化。但我始终觉得,在这种挑战中有一个没能完全克服的矛盾,即图像与你所追求的精神性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图像越丰富,有时候精神性的内涵就越会打折扣。因为当你不断回想马列维奇“白上之白”的绘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很啰嗦。这样一种绝对的精神,是很难企及的。因而你就会思考,新的精神性在哪里?如何表述?用什么方式?当然不是马列维奇的方式,而是你的方式,去挖掘这种更加强大的东西。
贺:正因为您一开始就从“形式”出发,逐步走向了对绘画本体问题的探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您的作品续接了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实践的脉络?这条脉络由早期的现代主义者如林风眠、张光宇、吴大羽、庞薰琴这些人开启,后来在30年代末的战争环境里中断、后来又被49年之后的政治性主流所覆盖。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层面上,您作为海派画家的身份更值得被关注?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现代主义的脉络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区域繁衍发生的结果。
丁:我在80年代上工艺美校期间,一个是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现象是,那批30年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老艺术家的作品开始被拿出来展览,包括刘海粟、关良、吴大羽等等。其实我对早期现代主义这块一直是很关注的。比如我用于特里罗(Maurice Utrillo)的方法画风景,常常把关良的东西也加在里面,画松树实际上我都是学关良,关良的松树我最喜欢,还有一些洋房边上的竹篱笆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从关良的绘画里看到、学到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们既感兴趣,又在反思。比如吴大羽,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画家,有点意象画,那一代艺术家实际上都是这样。最早在1983年,我第一次在浙江美院看到了赵无极的原作,当时很兴奋,觉得他是华人世界抽象艺术的巨大突破者。我也用他的方法画过几张画,学习过一些他的东西。早期我也一直对媒体提到赵无极,但是今天再看赵无极,已经完全不喜欢了。他的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很甜、腻,太漂亮。我喜欢他60年代的作品,71、72年的也还可以,之后就完全不喜欢了。
所以,这些艺术家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引进来,又进行了地域性融合的前辈。这一段的学习,和对于特里罗(Maurice Utrillo)的学习是同期的,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油画没学成,第二年报考了国画系,就是想清楚了我未来的目标应该是中西融合。去国画系,可以补一点我不懂的东西。但是等真的从国画毕业之后,反而中西融合的梦也破了,因为觉得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贡献,它不是一个扭转整个中国艺术状况的巨大变迁。但这个太难了,我还没有找到突破的点。你如果看日本,会发现他们同样没有找到这种扭转性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我希望是处在与西方同等的位置和平台,而日本还是在西方的评价系统里面来认知他们自己的,比如说从日本动漫或者日本的情色文化里产生出来的东西,它是有点异国情调,但这种异国情调跟上世纪30年代的异国情调很像。中西融合实际上就是异国情调,对西方来说是东方的,但是语言上用的还是西方的。
今天物是人非了。你的理解力、你站的角度、高度和平台都不一样了。但是某种时代的、中国的精神,我仍然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可以进行表述。但是用什么语言表述?也许是目前语言的加强或者再寻找,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迁。这总是一个心结,确实很难,仔细追究下去的话,又要说到更宏观的背景,国家的经济能量、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艺术繁荣的普遍程度。日本为什么做不到?最主要还是他们缺乏本土的平台建设,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购买西方印象派的作品中去,因而搭建不起本土意义上的平台,整个的环境没有成长。反过来说,中国在未来有可能吗?现在只是感觉到一点这种趋势。
时间 | 2018年6月30日
地点 | 丁乙工作室
贺婧(简称“贺”):我们或许可以先从“观看”而不是作为结果的画面谈起。多年以来,您的作品无论经历了多少画面上的变化,一个不变的东西是它们都在致力于对一种“观看”的创建。这种观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要求观众不去预设任何联想或阐释的彼岸,而返回到观看本身。正如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那句“你看到的就是你在看的”(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那么对您来说,画家的作品和他的观看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丁乙(简称“丁”):在这个系统工作三十年,持续工作的时间很长、每天与画布打交道很近,也就是说,始终好像是沉浸在里面。对于这个过程,我觉得最容易解释的一个字就是“悟”——你总在想,这样沉浸在里面到底是要做什么?这么多年过来,最重要的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因为你是一个画家,你工作的重心是和画画打交道,那么无非就是要产生好的画。这种好的画可以说是用你的身体力行去沉浸、去表现、去揭示,同时这种感觉也通过你的画面传递给观众。一张画要怎么让观众看到的时候有惊喜,然后不断看的时候有更多的发现和感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画家要给你的绘画里面注入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是宏观把控,包括画面的结构、关联、气势、颜色等等;另一个就是细节,你不断地让观众去观看,他的目光在这样的画面上是不停移动的,这个移动其实是画面带给观众的,也就是说,画家赋予它每时每刻的变化。
当然所有这些都与我建立的方法有关。这种方法就是没有一个完全的焦点、没有中心,它本身就是散点式的结构,没有巨大的纵深感;有的时候又是非常平的,它是散发、弥散在整个画面上的。在传统绘画中,观众的视觉是由艺术家引导到一个焦点上的,会忽略周边的其他东西,因而在焦点以外的地方就是“暗”的;而当你将这些焦点去掉,让画面“平面化”之后,其实每个地方都是焦点了,即使在那些“暗”的地方,实际上是有着相同的笔触、方法和结构。所以这是我的方法和古典绘画之间不一样的地方。
贺:80年代中期,您的绘画实践开始于对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和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笼罩下的艺术实践的“不信任”,是在这种双重“不信任”的基础上,您希望寻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完全个人化的思考和实践方式,包括确立了“让绘画不像绘画”的探索方向。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的绘画道路是从一个具有否定性(而非继承性)的起点开始的?这个起点富有非常清晰的问题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您的创作并非是远离意识形态思考的,只不过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多是指一种绘画的观念性立场而不是社会性或政治性的。
丁:关于这个问题侯瀚如曾经有过一句话:“丁乙也许是最意识形态的画家。” 实际上这个就是当时的一种现状,上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系统都在寻找新的出口,艺术领域可能更敏感、动作更快一点。当时又正好是求学的时代,所以对未知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比如说对于西方当代艺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全貌,了解的都是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所以就特别想了解。当时除了通过很有限的画片去了解,还有非常少的翻译过来的西方艺术史。有一本叫《西方现代艺术简史》,时间差不多覆盖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本东西很薄,基本上都是黑白图片,但是在1982年,通过这本书就能基本了解西方的一个系统。看过之后,你就会觉得西方在差不多这样一百年的历史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就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站在新的角度上起步,既能够和西方互补,又能够和中国以往认知的艺术系统有所不同。在学校做学生的那段时间,我能感受到我们接受的艺术教育系统与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既有中国的传统,又有前苏联的一些影响,所以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实际上在这之前,我的知识结构在私下里是在学习巴黎画派、印象派,几乎写生都在试用这些方法,为我打下了技巧的基础。所以当你用这些基础技术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当时的主流绘画,比如说上海美术展览馆还在做的大型主题性展览,你就会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懂技巧,同时开始不信任这个现状。以这些为基础,你就很快想建立起一些东西。而我自己当时在学校的学习是在国画系。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先生在教我们,年纪很大了,在社会上名气也很大,采用的还是很传统的师徒制方法,通过临摹来学习。而我下课之后一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就开始画试验性质的抽象作品。但那个时候实际是比较混乱的,有感而发什么都画,可能仅仅就是一本画册、一本书让你产生了画画的灵感。因为之前没有考取油画系,我反而决定去学习一些不了解的东西,就进入了国画系。但很明确,我也没有想要成为国画家。在1986到1990年的这四年学业期间,我从未停止过当代艺术的实践。
贺:那么您跟余友涵老师学习是什么时期?
丁:那个时候就是受到巴黎画派的启蒙,1980到1983年之间。余友涵那个时候在工艺美校做老师,但他实际上三年里面也只教过我们摄影课,都没有教过绘画。82年就有同学把我带到余老师那里,我带着一大卷作品,他就会指点一下。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终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做艺术家。所以虽然读的是装潢专业 ,业余时间全都在画画,包括周末。我一般一个月回上海(市区)一次,其他三个周末都安排自己画点东西。余友涵那个时候在学塞尚、学印象派,很多画我都是看着他画的,包括81、82年开始试验抽象。所以从学习西方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很同步的,可能中间的时间差就是两三年,但可能是年龄的关系,他的理解比我深刻地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否定了国内主流的方向。
贺:从您早期对于周遭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变化的摒除;到1998年您忽然意识到上海巨大的变化对您产生的影响,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荧光系列”的创作;再到近些年,我们看到您的创作实践似乎又回到了更多朝向绘画内部予以探索的道路上。这几次变化之间好像是存在着一种由内向外、再由外转向内的过程。您自己现在如何回看这样一个轨迹?如果说90年代末的社会变化让您意识到艺术家需要与他的外部世界发生关系,那么到了今天,您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吗?当您自己的体系已经完全建构起来并且越来越成熟,所谓的“内”或“外”的关系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丁:艺术家的创作历程,有时候是有意为之,有时候你又想摆脱这种策略性的东西。实际上我有过一段非常长的观念时期,很有策划性,好像要树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需要绝对和自治,摒弃任何情感成分,它变得严格、极简,或者说是绝对理性。因为在早期,你就是要确立自己的风格,就想让绘画有意为之,保持住这样一种统一性。而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你会发现这样绝对性的东西并不能涵盖自己全部的绘画历程,必须有新的角度、新的看法,随着年龄增长也会有新的经验,让你的作品在三十年的历程里产生很多变化和枝节。所以在荧光系列的时期,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巨大的变迁刺激了我的创作,对于城市化的看法被纳入到我的抽象系统里。这个过程的确让我的绘画产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颜色上的,这种变化到今天仍然有,只不过它的性质可能已经有所改变。
近几年,我一直在寻找新的东西,很难定义。我隐约觉得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社会精神,这种精神跟整个社会巨大的转型有关,这种转型让你能够以更高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98年的时候,你只是以中国为视野,你只看到你自己的世界;而这几年我希望能将自我的世界、中国的世界真正放在国际视野里去看待,这个视野有点难以表述,这也是我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有点复杂。 近几年我旅行最多的地区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这些地区以前是不了解的。以前我们关注的都是发达国家、主流艺术世界,这些东西放到今天仍然重要,但你的视野应该更大。这些旅行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对于这些国家的不同文化给了我很大的补充和感触,原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了解。
另外一个是发现中国制造业的力量在第三世界扩张地非常厉害。制造业已经是中国的主流,而相比之下,艺术、文化仍然不是。你如何承担这个东西呢?当你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有主导性的同时,文化上是否能具有真正意义的主导性呢?我们的文化还是很弱的,缺少文化自信,也没有真正具有全球性认知的价值观,能够去拓展新的文化体。所有这些,都让我思考在绘画中你要追求什么,全球化的语言和价值观在哪里,这个很复杂。比如说,“一带一路”主要就是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经济扩张,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但缺少文化的先导。所以我觉得文化在今天变得尤其重要,需要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思想不强,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发力。但是作为一个画家,很难有办法去改变整个局面,我只能感受到这种可能性,让它在创作之中有所呈现。可能目前我在探索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希望在作品中能有一种能量的爆发,同时又是使用很中性、抽象的符号,但是可能能够把这个时代的某种雄心保留下来。
贺:侯瀚如曾经说过,您作为个人主义艺术家的可能性,是在上海这个城市才得以成型;也有画廊家认为,“丁乙的画作只可能诞生在上海”。您自己认同这个观点吗?
丁:从个人感情上,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我终生居住在上海,也从没有意愿离开上海,这些可能是缘于我对上海的熟悉、对这个城市生活的满意。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很多创作灵感也来自于上海。对于这个城市的变化,每一次的转折我都能感受到。我不知道侯瀚如的评价对我意味着什么,但是从我日常的工作来说,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上海能让你感觉到最喧嚣的、最繁荣的大都市气息,而你进入工作室的时候,你可能又是被社会遗忘的。它使我既能保持独立性,又能与世界相通。
贺:谈到城市与艺术家创作之间的联系,您的创作反而让我更多想到上海这个城市与中国早期的工艺美术传统、设计之间的亲密关系。您似乎从来不排斥“工艺性”这个被很多画家、前卫艺术家所忌讳的问题,您个人也有过从事设计工作的经验。那么,这种与工艺、设计,与现代都市紧密关联的基因,对您而言更多是来源于个人化的东西还是来源于上海的都市传统和环境本身?
丁:跟上海的环境和我个人经历都有关系。上海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亚洲最繁荣的城市,这种繁荣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城市时尚的理念,这个理念与当时的巴黎、纽约、东京都是一体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你对审美的追求是带有时尚化的,也就是说,你对所使用的物品、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带有品质的要求。所以为什么有所谓上海是中国最洋派城市的说法?因为它最接近于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反观80年代,中国很多城市都不太像城市,有点像农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与现代都市是直接相关的。当然,当代艺术的命题除了关注人性、精神层面,还有一些形式的东西,这些东西与都市文化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上海,好像从出生以来,周围的环境就会让你投射到一个国际视野里面,这造成了在很大层面上,你都不会去跟国内做什么比较,比如你的创作就根本没想到要去参加北京的展览,而是去参加纽约的、伦敦的展览。这种意识很可能从你的前辈一代开始就是这样了,我觉得它可能是非常潜在的。
贺:您的创作最为清晰的一个特征在于一种重复的节奏感,当然这种重复不是原地复制,而是在重复中生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一方面这种重复迫使整个绘画系统发生了一种均质化的样态,也就是汪民安老师曾经提到的“一张画是另一张画的共振”;而同时间,重复的不断发生就促成了演进。就像是一种微观上的静态最终引发了宏观层面的动态,从不变中生成了变化。这种绘画行为本身富有很强的观念性。那么对您而言,这样一个经年重复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绘画行为,是否比最终的画面本身更重要?
丁:有时候我一天画下来,感觉自己这个方式很像传统的画家,虽然脑子在转,但行为方式很传统,花大量时间融在创作里面。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我的灵感之源就是这些工作本身。每一张作品的变化都是跟前一张未能完成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当完成了一张画之后,就会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或者当一张画没有完成的时候,它也会生成对下一张画的作用。比如《十示 2018-1》,画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忽然觉得这张画的场景很像我去年在敦煌看到的雅丹地貌——它实际上就是几百年的风沙把一些自然的山侵蚀掉。那么我就觉得类似这样的一张画,应该再画一张更大的,场景上更丰富的。同时,这张画在图形上也有一个突破——原来更多是在平面中隆起的,而在这一张中就产生了希望它有一种斜向冲击力的想法。而当更大的这张画《十示2018-2》完成之后,我就开始想,用什么方式来改变它的基底的东西,于是在下一张中,就开始对色彩进行重新配置,而为了让这个配置更为清晰,你又觉得这里的色彩必须是一个淡色调的…… 就是这样,产生了一种画与画之间相互作用、推衍的过程。
贺:所以说是从这个推衍的过程产生了画面本身?
丁:是的。创作的变化和演进,这个演进可能包括在材料的寻找上、色彩的配置上、技巧的变化上。但不变的是一张到下一张,一张未完的问题再到下一张的问题,真的是推衍的过程,三十年都是以这样推衍的方式在创作。
贺:您曾经说过,希望“绘画仅仅回到形式的本质,形式即精神”。在“十”字形这个构成您几乎所有画面的最基本的元部件上,似乎看到了这句话的印证。您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使“十”字丧失了它的符号性,即切除了它的所指,使它仅仅成为了一个形状、一个构成画面的纯粹的形式,而这个元部件的繁殖、变化和推衍构建了您的创作系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绘画从最初的起点开始就是“极简主义”的,它同时呼应了(前面所提到的)观看机制层面的“极简”。或者说,无论最终的画面如何呈现出一种色彩丰富和形状的“繁多”,您的作品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始终都是极简主义的。
丁:起步的时候跟今天比,从表面来看更极简。当时的方向很明确,要极简,更平面,因为极简无非是形状的最简单化,还有一个是画面的绝对平面性、色彩的最低限度,无非是这几条。那么我自己还是把自己定位在极简主义的艺术家里,但是这种极简与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极简,或者是之后斯特拉这些六七十年代的极简,已经是不一样了。
比如说马列维奇在一百年前的时候已经做到了真正的极简,就等于说这个门被他封死了,黑上之黑、白上之白,已经完全没有余地了。而我所说的极简,是如何在最低限度中达到绘画性的调配。比如色彩,我用荧光色创作了十二年,它的整个色系差不多只有四到五种颜色,十二年的时间里都是在这种极简的色系里工作;另外所使用的符号,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元,十字或者米字,据此工作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极简。
贺:您一直在强调关于精确性的问题,它代表了绘画理性通道的产物。在早期,您借助尺、鸭嘴笔这些工具来寻找这种精确的概念;而近年来,精确性在您的绘画中表现为一种推衍的成像方式、一种元语言(“+”和“x”)的综合算法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认为您的作品与传统概念上的“抽象绘画”是存在距离的,前者更多是在以形式和色彩的表现来生成对描绘性、叙述性的反抗,而您近年来的作品不仅仅是基于形式和色彩的,它存在着一种更富有当代成像机制的基因。
丁:我也一直在反思,今天的当代艺术、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它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图像学的角度,需要有一种“新”的图像,抽象艺术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去分析中国前三十多年的当代艺术实践,你会发现在图像学上出现了问题,那种图像学的指向性是短暂的,它只是社会某种小情绪,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反应,所以它所产生的图像缺乏永恒的价值。在抽象领域里,因为抽象图像本身不太直接对应于社会现实,所以自由度更加宽广。某种程度上来说,抽象艺术是最容易“上手”的,但也是最难的艺术。从最初开始我们能看到两种抽象:理性的,或者感性的。感性的抽象,因为它是抒发性的,任何人都有抒发的理由,都有抒发的能量,他可以一挥而就,但持续性是最大的挑战,这种持续是不是可控的?让自己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画里,这不是一时的状态可以把控的。所以有时候在国内很多抽象艺术的群展上,我们会看到边上的作品让你感到从图像学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旧的图像、以前的图像,它自身缺乏挑战性,这是从时间上来说;有时候还会有诸如纽约的抽象、亚洲的抽象这样的说法,这里还有了地域性。抽象绘画的领域里往往就会有这些东西。而对我来说,一种新的、这个时代的图像,一种能够体现我自身独特表现方式的图像,才是我最最在意的东西。
贺:谈到工艺性,您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组看似矛盾的东西:一是求于认知层面、直达图像之物性探讨与语言结构的绘画;而另一个则是来自工艺美术传统、孜孜耕耘于纯粹技术层面的制图之术。这是两个看似难以相接的端口,是如何在您的作品中同时存在并且达到互通的?
丁:我自己是很迷恋这种矛盾性的。我对绘画的评判原则,一个是“正”。一张画一定要“堂堂正正”,不要耍小聪明,不要做手脚,甚至是做肌理,去埋设什么东西,必须是非常正气的、正向的这样一种状态。包括创作中的时间性因素(不要有速成的心态),都是保持所谓“正”的一种主要配置;第二个,在“正”的前提下,我一直希望作品“不顺”。它不是要流畅、顺畅,或者好看、优美,这些东西我是否定的。要很不顺的,里面有一些骨头。是这些东西让一件作品在“正”的前提下会有些“歪”,有点怪,在设计里面有种东西,设计与绘画结合可以调配这种不顺,你看绘画也不像,设计也不像,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
另外绘画不能指向性太明显了,它需要有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也许是模棱两可。艺术家有时候用语言很难完全阐释清楚,但是他的图像是能让观众有所感受的,而观众的感受可能也是模棱两可的,也不能像数学那样明确,有绝对的答案。
贺:所以您认为工艺性,或者这种带有技艺层面的东西,其实是在帮您调配“正”与“不顺”之间的关系?
丁:是的。但是同时这些年来,所谓我的风格,就是由这几个因素组成:第一是格子,整个画面做了格子;第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线来表述的;第三,“+”字或“米”字符号。这三个东西构成了我的风格,区别于其他艺术家。其他的都是历程的变化,而这三个东西代表了我创作的基本面貌。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带着设计性的,所以从创作之初,这个设计性就跟随着我,一下三十年。
贺:作为一位画家,身体与您的作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显然在您的系统中,身体既不像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中那么富有存在感,同时,观念和技术上的理性设置也无法完全抛弃身体的介入。比起那些表现性的、激情洋溢的画家,“身体”问题在一位常年重复着相似的绘画动作的画家那里似乎要复杂得多。
丁:是的,更复杂、更内在了。抽象表现主义的动作是外化的,是可以表演的,动作的起伏可以更加富有节奏。但是实际上类似像我这样的作品,更多是一种身体的、持续的动态性工作。抽象表现主义之所以成为行动画派,是因为它的动作幅度很大,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它是腰的动作更多,我是手臂、或者说是手腕的动作更多。我想艺术不应该是由所谓的动作性来评判,不是说身体的某个部位动作幅度越大,它所产生的动能就越大。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是“微观”与“微微观”之间的微妙关系。动作的痕迹都在画面里,只不过我的作品更加微观。从工作状态来说,也许像这种微观的创作,它所产生的体力的持续性更强。因为你一工作就是10个小时,如果换成是波洛克可能已经完成三张画了。
最近这几年,我的工作状态特别好,特别想工作,而且停不下来,能让自己真的沉浸进去。在早期,也就是在1991年那段时间我有过一段这样的状态,我现在觉得这个状态又回来了。你能够有很完整的时间完全投入其中。91年那时候,我通常是下午开始工作,有时候工作到晚上八点钟,就骑自行车随便去看个什么电影,十点钟再回到工作室继续画,一直到早上四点。那个时候工作和生活完全在一起,所有生活都是围绕创作,这是最好的状态。我现在的状态和那时候差不多,所有时间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创作,然后累了午休半小时,但是你所有的精神状态、思想状态,所谓的时间的主要分布,都是围绕着创作,所以这真的是最好的状态。
贺:到今天为止,您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吗?我们知道您在很多年的实践中,反复试验了不同的材料、技法,包括对于绘画所作出的不同限制与开拓。而近几年我们看到,表面的、技术性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少了,您更多在针对“结构”本身在处理问题(而并不简单是“越来越抽象”的问题)。
丁:当然有,这个难题或者说是不断推衍的。一个是创作的状态,一般来说创作状态是有起伏、有峰值。近几年,这种峰值不太明显,当然我在靠一些外在的东西在“吊”着它,比如展览,每年一个大展览,让我调动所有的能量、激情、工作状态来进行工作。
每年给自己设定的展览里都有新的作品,这些新作品和上一年之间的变化,也是一种变化。同时并进的是,除了图像的变化,还要有更深层东西的思考在进展着,包括视野的变化。但我始终觉得,在这种挑战中有一个没能完全克服的矛盾,即图像与你所追求的精神性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图像越丰富,有时候精神性的内涵就越会打折扣。因为当你不断回想马列维奇“白上之白”的绘画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很啰嗦。这样一种绝对的精神,是很难企及的。因而你就会思考,新的精神性在哪里?如何表述?用什么方式?当然不是马列维奇的方式,而是你的方式,去挖掘这种更加强大的东西。
贺:正因为您一开始就从“形式”出发,逐步走向了对绘画本体问题的探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您的作品续接了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实践的脉络?这条脉络由早期的现代主义者如林风眠、张光宇、吴大羽、庞薰琴这些人开启,后来在30年代末的战争环境里中断、后来又被49年之后的政治性主流所覆盖。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层面上,您作为海派画家的身份更值得被关注?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现代主义的脉络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区域繁衍发生的结果。
丁:我在80年代上工艺美校期间,一个是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现象是,那批30年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老艺术家的作品开始被拿出来展览,包括刘海粟、关良、吴大羽等等。其实我对早期现代主义这块一直是很关注的。比如我用于特里罗(Maurice Utrillo)的方法画风景,常常把关良的东西也加在里面,画松树实际上我都是学关良,关良的松树我最喜欢,还有一些洋房边上的竹篱笆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从关良的绘画里看到、学到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们既感兴趣,又在反思。比如吴大羽,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画家,有点意象画,那一代艺术家实际上都是这样。最早在1983年,我第一次在浙江美院看到了赵无极的原作,当时很兴奋,觉得他是华人世界抽象艺术的巨大突破者。我也用他的方法画过几张画,学习过一些他的东西。早期我也一直对媒体提到赵无极,但是今天再看赵无极,已经完全不喜欢了。他的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很甜、腻,太漂亮。我喜欢他60年代的作品,71、72年的也还可以,之后就完全不喜欢了。
所以,这些艺术家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引进来,又进行了地域性融合的前辈。这一段的学习,和对于特里罗(Maurice Utrillo)的学习是同期的,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油画没学成,第二年报考了国画系,就是想清楚了我未来的目标应该是中西融合。去国画系,可以补一点我不懂的东西。但是等真的从国画毕业之后,反而中西融合的梦也破了,因为觉得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贡献,它不是一个扭转整个中国艺术状况的巨大变迁。但这个太难了,我还没有找到突破的点。你如果看日本,会发现他们同样没有找到这种扭转性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我希望是处在与西方同等的位置和平台,而日本还是在西方的评价系统里面来认知他们自己的,比如说从日本动漫或者日本的情色文化里产生出来的东西,它是有点异国情调,但这种异国情调跟上世纪30年代的异国情调很像。中西融合实际上就是异国情调,对西方来说是东方的,但是语言上用的还是西方的。
今天物是人非了。你的理解力、你站的角度、高度和平台都不一样了。但是某种时代的、中国的精神,我仍然希望在之后的道路上可以进行表述。但是用什么语言表述?也许是目前语言的加强或者再寻找,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迁。这总是一个心结,确实很难,仔细追究下去的话,又要说到更宏观的背景,国家的经济能量、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艺术繁荣的普遍程度。日本为什么做不到?最主要还是他们缺乏本土的平台建设,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购买西方印象派的作品中去,因而搭建不起本土意义上的平台,整个的环境没有成长。反过来说,中国在未来有可能吗?现在只是感觉到一点这种趋势。
开放信息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通过微信公众号实名注册预约,到馆出示预约二维码、预约人身份证进馆。如需预约改期请先取消预约重新预约。每个成人限带1名儿童(未满14周岁)。
目前仅接受散客(个人)参观。
热门文章
-
金秋十月第一天,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以一场庄重而盛大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
图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