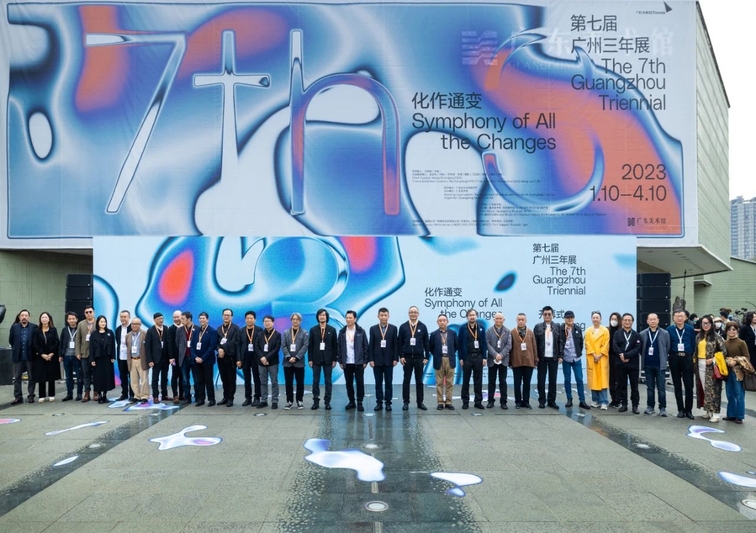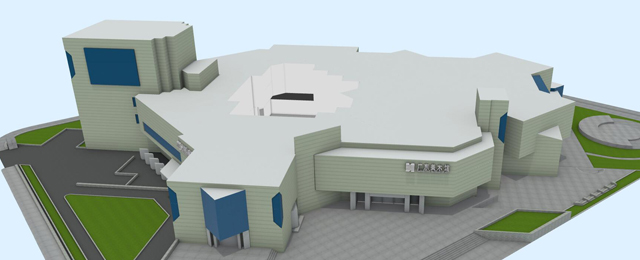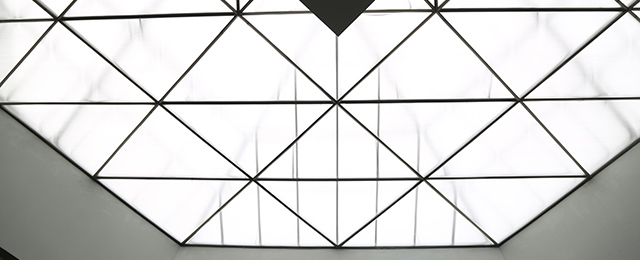资本时代与山水精神——关于第三届广东画院学术提名展(陈迹)
录入时间: 2010-11-30
这个展览所要呈现的,是在城市化和资本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山水画家在“山水精神”的理解上与传统“山水精神”的异同,以及不同地域画家和不同个体之间对于“山水精神”在表现上的差异性。
中国绘画史告诉我们,自唐末五代文人画逐渐兴起之后,山水画在传统绘画中的地位便越来越显要,到了明代董其昌时候“南北宗说”在绘画领域上的正式提出以及董氏对南宗绘画不遗余力的推崇,文人山水画的正宗地位更在理论层面上得以确立,并几成一统中国画坛之势。关于传统文人山水画,笔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从历史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宋元明清以来占画坛主流地位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存在着与中国传统社会相近似的宗法制度,也即是他们渊源有自的传承性和正统性,这无疑是受到文人画作者的主体——文人士大夫们所秉承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技法和图式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传统文人画在精神指向上,则更多地受到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道、禅思想的滋养,孤寂、虚空、旷远、明净这种以沉静内敛为指归的审美境界,则成为士大夫画家们所普遍追求的共同理想,这种追求有着强烈的“哲学”层面上的意义——这或可视为士大夫们公务之余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自我平衡和逃避。”①
如众所知,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是入世的,要求人们遵守社会秩序,提倡责任感和社会担当。“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比德”则是儒家重要的美学内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在儒家看来,隐然已经有了人格的精神和人生的意象。当然,这种精神意象并非自然山水本身所固有,而是儒家所谓的“比德”——将自然山川人格化。道家则崇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显然,这是一种与儒家完全不同的出世的思想,它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浸润交融,来追求社会人生羁绊的解脱和灵魂的释放,并因之达到生命澄明的境界。晋宋间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就曾经这样承认:“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②与谢灵运大约同时代的画家兼美术理论家宗炳(375-443),也在他的《山水画序》中说,“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在这里,宗炳首次提出了山水画史上“畅神”这一重要概念。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受到儒、道、释多重影响,他们游山玩水,“比德”“畅神”兼而有之,人与大自然山水之间也并非如后来通常所谓的“主体”与“客体”关系,而是共生共存于宇宙天地之间而无丝毫隔阂。这种关系表现在绘画上,则“山水”之于人,出入自由
“可居可游”,人因山水而物化,山水也因人而人格化,人既可“卧游”于山水之间而“天人合一”,又能出入自如而觉悟宇宙人生的真义;以上这些,再加上由禅宗“不离世间”而“明心见性”等精义所引申出来的“意境即心境”等观照山水的方式,大概就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最具东方文化特质的“山水精神”。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绘画中的“山水精神”,是一种远离社会性活动和拒绝社会功利目的的颇具哲学意味内省式个人体验。然而,这种“非关世用”的山水画创作形式,在上个世纪之初因了社会革命的兴起而出现的新美术思潮——尤其是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1919)、陈独秀《美术革命》(1919)、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1920)等这类檄文式文字的相继出世而构成的“延西治中”这一具有强烈功利色彩中国画现代化主流革新方案冲击之下,失去了其社会学的基础而逐渐走向式微。1949年之后,由于受到泛政治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政策所规范,以讴歌新社会新建设和赞美祖国大好河山以及以“革命圣地”和“毛泽东诗意”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新山水画”,成为几乎唯一合法的山水画艺术形式并一直延续至1970年代末期。“随着1980年代之后西方文化艺术的全面涌入,突然面对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而又陌生和变化莫测的西方文化世界,许多艺术家在兴奋的同时,有一种无所适从和痛楚之感,对充满诱惑力的‘西方’的认同,也将意味着对充满威胁的‘他者’、‘非我族类’的认同。对于中国画领域的讨论和创作而言,无疑多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般的参照物。1980年代中后期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论争中,复兴中国文化,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命题,也是中国画领域的一大命题。后来出现的新文人画和实验水墨等,都可视作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之下有组织性、策略性的文化回应。”③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画家们以现实政治为旨归的山水画创作理念,至此“集体转换”为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在作品上则体现为普遍存在着人文关怀和文化理想色彩,而这种人文关怀和文化理想色彩,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之后则逐渐为市场经济所消解。“1990年代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与收入挂钩的政策,更是在经济上牵扯和规训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位公民,于是,‘赚钱’越来越成为各阶层共同的目的,作品能够赢得市场,也成为众多画家的‘共同理想’”。
④
诚然,当画家们连自身的生存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强求他们担负起提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可是,一个画家如果热衷于依附资本,那他的精神质地也必然会趋于苍白和逐渐失去“自我”。近年来,在全球化和资本时代背景之下,坚守山水画的人文气质,以新的“山水精神”观照自然叩问人生,成为不少山水画家的自觉,不同地区和个人,这种自觉又表现出相当的差异性。
本次提名的作者中,西安崔振宽的作品尤其专注笔墨本身的内在力量和画面整体的形式美感而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力。记得大约在八、九年前的时候,崔氏曾经来广州的广东美术馆举办过个展,其雄深苍润笔墨和浑朴画面,给笔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当时崔氏的山水画尚多黄宾虹痕迹的话,那么,这次所出品的“焦墨山水”系列,则在黄氏基础之上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纵横离披而又古奥单纯的点、线所构筑而成的强悍画面,传达出西北大地的沉郁和苍凉。
相对于崔氏干笔渴墨所形成的苍茫之美,出身于“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的何加林、张谷旻、丘挺三位画家的笔下,则是“一片江南”胜景。他们用笔用墨传统而纯正,笔者以为,这与传统绘画中的南宗一脉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在此绵延不绝至今有着非浅的关系。当然,三位的个性风格也是各异的,概而言之,丘挺用笔流美疏秀、用墨淡净轻清,他惯用渲染手法营造意境,画面有出尘之感;张谷旻多用迟涩而不确定的线条来构造江南名园中常有的亭榭、回栏、曲径、古树,错落其间的宿墨笔触所点染出的清润中的斑驳,使人依稀王谢旧家;何加林以笔御墨,涩而能疾,勒而能松,朴茂中见空灵,沉实中显松秀,其笔下荒村野水,廊桥古渡,使人恍如置身水墨江南。以上三位的山水画都远绍传统而饶有古意,又能古而不旧,显然,这与他们经常写生密切相关。从三位的绘画实践和成就来看,“继承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样的“陈词滥调”,依然有着现实启示意义。
范扬也出入传统,但他似乎更乐意于对传统笔墨进行“误读”。他的山水画笔墨雄奇,但细细品味,又并非传统笔墨的那种纯正;他的画骤眼望去,似乎有董其昌和黄宾虹的影子,但细看时,又似乎不是。对于范氏来说,“写生”与“创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的写生取景角度通常较为奇特,用笔也恣肆热烈,与西方后印象派画家在精神气质上有某些近似性。相对于范扬激扬飞动的笔墨线条,林容生则有意弱化线条的独立存在价值而让块面走上前台,他以青绿山水描绘苍绿湿润的南方家乡,并有所节制地引入写意画的笔墨意趣,画面温润而整饬,富有装饰意味。
参加本次展览的李东伟、方向、张彦、李劲堃,均曾求学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而广州──尤其是广州美术学院,一直以来就是以写实主义手法改造传统绘画的岭南画派大本营;在教学上,深入生活写生尤其为广美中国画系所重视,并被视为教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⑤毫无疑问
,“写生”对于他们几位后来绘画风格的形成,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如张彦本次的出品,即全部是“以写生为创作”,但这些作品显然又与“以在写实主义语言结构中充分地展现大自然直观的美感为特征”(李伟铭语)的岭南画派前辈画家们大不相同。张氏的写生更加注重自己理想中的山水图景,变化无穷的大自然山水,不仅是张彦描绘的对象,更是他笔墨精神的操演之所——张氏自己谓之“借山还魂”。李东伟虽然也重视写生,但那只是他亲近大自然的一种职业方式。如果说,富有激情和历史使命感的他那具有经典意义的“静观系列”,“画面上那来自西方现代艺术结构图式的经验启发与有着强烈东方文化意味的特定符号──瓷瓶、青花、笔墨、山水的并置和错愕,是他在那西方现代艺术之风最为炽热时候的自觉文化反应,其视点主要还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之下一位艺术家的文化立场上,那么,他后来的‘中国乡村系列’、‘旧街市系列’等,则将观照的角度返回到城市化进程铁轮倾轧之下中国农村和古旧街市等人文景观的变化,并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变化予以持续的关注和人文思考”。⑥相对于李东伟的文化英雄主义情结,方向的绘画无疑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温馨,以及画家对这种日常细节的娓娓道来中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从温情的南方水乡到雅致祥和的农家庭院,以及由农家庭院延伸到都市庭园式那富有情趣而又不乏小资情调的闲情安逸,都可以视之为方氏对他为之追寻的理想家园的艺术营造。李劲堃在广美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是岭南派的黎雄才和陈金章等先生,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岭南画派著名山水画家。然而,这种家学渊源和师承,并没有使他沿着前辈“写实主义”绘画风格的轨道继续下去,而是在溯源唐宋的同时将目光伸向域外。笔者以为,他的山水画虽然多有采用写生得来的素材,但其图式和用色用墨的反复渲染,多受日本绘画的启发;而对色调和色层的会心,则得益于他深厚的西画功底。
如果说,前文所述这些画家所描绘的山水,毕竟还是人世间景象的话,那么,卢禹舜和许钦松笔下展现的,却是虚无邈远的地老天荒。卢氏这次出品的《天地大美•心驰神往•笔随墨顺》系列中那超越现实时空的静谧神秘世界,让人有不期然而置身于天地鸿濛时候那可居可游的桃源胜景而有“穿越”的惊喜。而许钦松笔下那厚实雄壮的山体以及山水之间、天际之外的云涌雾动所形成的壮阔博大之美,则是一种自我完足的生命状态,在这里,“人”对于“自然”,是一种“隔岸”式的观照,虽然心向往之,然而,却是可望而不可即。
与以上颇负使命感的诸位山水画家不同的是,作为以人物画名世的尉晓榕,涂抹起山水画来却是那样的悠然率性。他的山水画在图式上虽然也有现代构成的意味,然而,那雅净的色调墨痕,以及那兴之所至笔随意走的蓬松笔调和自在心境,在笔者看来,反而更为贴近传统文人画之旨趣。而姚鸣京这次展出的“坐忘”一类作品,云浮水动,佛龛塔影绰约其间。虽然大家习惯上也将之归入山水画,但笔者以为,那其实只是他的梦境,是他的笔墨之梦,也是他自己心象之外现。静夜钟声梦中之梦;澄谭月影身外之身。何者为幻,何者为真?姚氏的绘画,处处禅机。
笔者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大约这样说过,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笔精墨妙可居可游,有一种牧歌式的宁静,然而,这一植根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并由此形成的审美定势,已经难以激起现代都市文明之下人们内心的共鸣;另一方面,现代都市的喧嚣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又使人们对原始的大自然有着无限的向往。然而,以往那种“自然即我,我即自然”的生活状态,在社会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当下,却悖论般地成为现代都市人的一种奢望,于是,重返大自然,成了时下一种强烈的呼声,对于中国山水画家来说,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具有现实指向和史学意味的命题。⑦
毫无疑问,现在的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关系,显然,这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哲学价值理念密切相关。现代哲学普遍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表现在社会现实生活实践上,则是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与利用。曾经的移山填海、战天斗地那新社会新建设恢弘场景,想必年长一代依然历历在目;而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当下,自然资源开发无序,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土地等备受污染,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概已经没有人意识不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了。所有这些,无不提示着我们必须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
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经这样强调:“不要去发现什么,而是要去拾取我们丢失的东西。”是的,曾经的功利主义使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精神受到普遍的弃置,而在“人”与“自然”处于紧张关系的资本裹挟一切的当下,以中国文化立场为出发点的“山水精神”,似乎在向我们提示着一个曾经的通融世界。
陈迹
2010年11月11日草于留留书屋
注释:
①陈迹:《我在:一种自觉的南方品格》,广东画院编:《第一届广东画院提名展》,第8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04。
②谢灵运:《游名山志》,《全宋文》(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3册)卷三三,第1页。
③陈迹:《我在:一种自觉的南方品格》,广东画院编:《第一届广东画院提名展》,第9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04。
④陈迹:《小议美术界的“商标化”现象》,《美术观察》
⑤陈迹:《品质·文化·生活──广东青年新状态》,《重置·传统:学术邀请展》,广州: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08。
⑥陈迹:《四合:读李东伟、陈映欣、黄国武、方向绘画》,《四合:李东伟、陈映欣、黄国武、方向》,香港:三度出版有限公司,2009.01。
⑦参见陈迹:《“实在之境与生命观照——读许钦松山水画近作》,《当代中国画》2007年第四期。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近日,“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首讲在广东美术馆新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