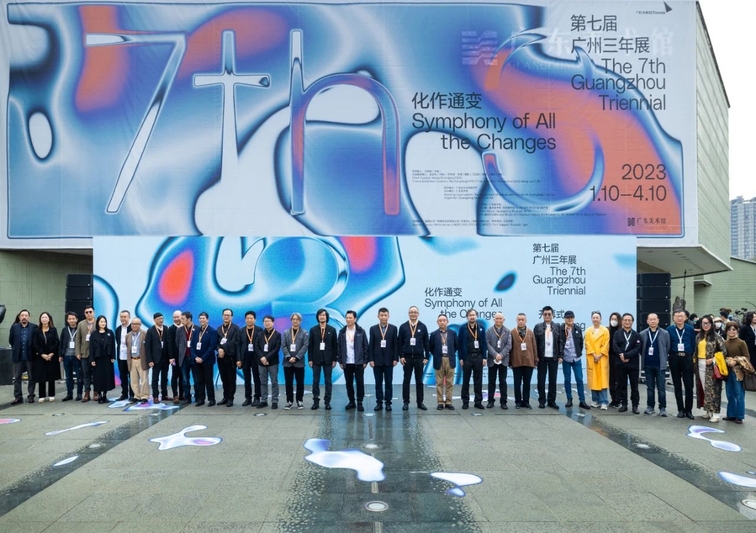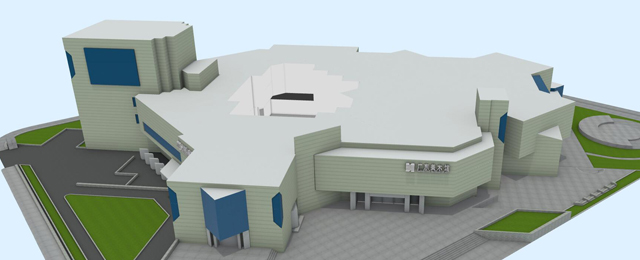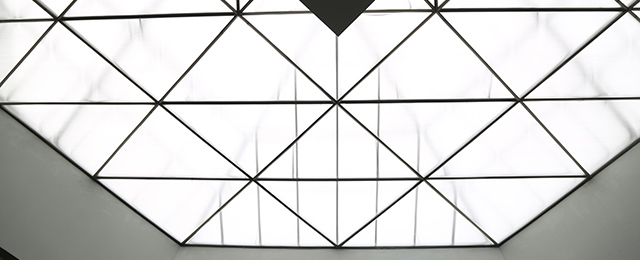写生:书写与视觉的双重关联(王璜生)
录入时间: 2006-11-30
(代序言)
文/ 广东美术馆 王璜生
2006. 11. 24
在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看来,人所创造的语言符号,其重要的特征,不只是在于它本身内部和它同所表达的对象之间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语言符号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包含着当场显示和未来在不同时空可能显示的各种特征和功能。正因为语言符号中隐含着这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也就是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特征和功能,才使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差异化问题。
“写生(painting from
life)”,现在普遍流行的看法,是指直接描绘实物对象的临场习作。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写生的原意为不依粉本而直接描绘活的花果、禽鱼、走兽等,宋代的“赵昌写生”就是这一词汇的典型所指;而在西方,传统上有没“写生”一说,没细考,但以描摹客观对象为能事,也可见西方对于“写生”的美学意义。刘小东此次展览取名“写生”,从直接的所指上看,似乎再简单不过,就是直接对人对景绘画;但是,深入辨析,可以发现刘小东试图通过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探询“写生”本源两种似乎相冲突的逻辑,即它同时具有表达的书写性和描摹的绘画性。
首先,写生,是由身体的具体动作而产生和留下的笔触、线条,它们类似于语言的“音素”,是可能产生语意的单位,但在其未完成(成形)、未及意义形成和显示主题前,它们是不可见的。因此,“即使描画是摹仿的,即复制的、具象的、再现的,即使模特被置于艺术家的面前,痕迹也必须在夜晚展开。它逃离了视觉的领域。”(德里达),即是说,书写动作的实质是记忆的和非生产性的;另一方面,随着这些身体动作痕迹的组合、连接和展开,即造型的出现,出现了类似于语言中的语意-句法的产生-在描画的痕迹中便有了场景、再现和叙事可能。但是,与此同时,那作为造型或意义产生的前提的每一笔、每一点、每一条线条,即痕迹,又逐渐消失,成为不可见的。“后撤或遮蔽,痕迹的有差别消失。”(德里达语)任何“书写”都与视觉经验有着双重的关联:一方面,页面上的标记如同绘画一样呈现在眼前,是真实事物的可见展开;另一方面,以其厚重的物质性,这些标记遮蔽了被视为纯粹精神世界之透明窗口的语言的直接性,从而导向那两者之间不可见的断裂。对于绘画文本来说也是如此,随着描画的痕迹如同文字一样不断产生、增加和重叠,线条/形象在画家和观者眼中不断呈现和消失,在描绘出的事物和描绘的痕迹之间,再现的东西与其再现之间,模特与形象之间,便出现了什么也看不见的“黑夜”。心理学告诉我们,
人的意志的本性, 就是去知( savoir ) 和去看( voir ) 的意志。但, 《约翰福音》上说, “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基督教导人们如何去看( voir ) , 如何去知(savoir ) 时,
认为如果(人)心中没有信仰,没有记忆,没有祈求,没有感恩,即使有眼睛可能也无所见。所以,手与眼及隐喻,触觉与视觉的关系不仅是描绘,同时也是书写的一个中心问题。(《书写与差异》)德里达认为,书写并不是对于已经看到的形象或已经知道的意义的如实再现或直接表达,而是对于未见的形象和未知的意义的一种预期,一种触摸,一种探索,一种感觉。它首先与手相关,是手的操作、动作和举止,或者说就是手术。在这里,德里达想到是手(main)与操作(manipulations)、动作(manoeuvres)和举止(manieres)之间在词根上的联系,而手术(chiurgie)一词则来自希腊词:手(kheir),其字面意义就是“手的工作”。这也就是说,书写不可能是思想的直接呈现,必须通过手的动作(词语/造型的产生)来实现。由于这一过程的存在,意义和其痕迹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永远存在着时间/空间的延异。艺术家的书写本来就出自身体的记忆,通过书写这一行为,他们将自己的全部感觉、情感和欲望铭刻在页面上。就西方的绘画传统而言,绘画是依靠视觉对于眼前事物的直接描绘,西方的绘画艺术就是起源于这种凭借视觉所进行的如实再现(实物)。在普林尼《自然史》中记载,西方第一位画家是出自希腊城邦的布塔得斯(
Butades
),他曾将恋人的轮廓借烛光投影在墙壁上,然后加以描摹。在德里达专门研究了卢浮宫两幅以此为题材的绘画,分别题作《布塔得斯或素描的起源》和《布塔得斯临摹恋人的肖像或绘画的起源》时发现,在这两幅画中,布塔得斯都没有看她的恋人,不是她背对着他,就是他转过身去,他们的视线根本无法相对。这就好像描画时是不能看的,就好像人们只有在不看的条件下才能描画。更重要的是,“不管布塔得斯追寻的是一个影子还是轮廓的痕迹-她的手有时是被爱神所引导-或不管她在一面墙的表面或一幅纬幕上描摹,手的书写或影子的书写都开启了一种盲目的艺术。从一开始,感知就属于回忆。”显然,在这里,描摹被视作一种姿势语言,协调着身体的记忆的是触觉而非视觉。无论艺术哲学还是宗教学的研究都表明,人类造型的本质是对于债务或赠予而不是再现的信守。更准确的说,对于承诺的信守较对于再现的信守更为重要,
如那些纪念碑的造型是由治疗、展现、讲述、书写和感恩的词义构成。“
书写通过记录,通过将其托付给一种在表面的雕刻、沟痕、凸显而产生意义,这一表面的根本特征在于去无限地传送。”
因为“只有人知道如何超越看与知,因为只有人知道如何哭泣。……只有人知道如何看到这一点-眼睛的实质是眼泪而非视力。”(德里达)这表明了一种书写与身体的关系,正如,威廉.法克斯在长江三峡的写生现场叙述刘小东创作时所说:“……他的动作虽有思考但又非常迅速,有时候,我也惊讶,他脑海中的景象丛他手中快速地构成,使我不能意识到那白、蓝、绿和褐色会落在何处”(《在江上》),“写生”由于具有了书写和描绘两方面的特质而成为一种记忆物而非视觉物。
问题是,这记忆传送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形象还是文字的描绘,首先都不是对于事物的再现,而是对于某种承诺的信守。刘小东在早期画过一些自画像,也许没有什么比自画像更能说明作品文本的幽暗、破碎和断裂的性质了;当画家描绘自己的时候,既是艺术家,又是被描绘者(模特),既是动作(描绘)的主体,又是被描绘的客体;既在观看,又被观看。由于艺术家在画自画像的时候是处在观者的位置观看,所以,艺术家的自画像只能是为他者存在的“自画像”。在这里,艺术家的主体,作品的署名人,便变得含混不清。在自画像中,观看这一行为也成为一种不可实现的企图,因为在观看“观看”时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什么也看不到。“这观看的眼睛看见自己是盲目的”,自己已然投入到黑夜之中;这也如“写生”这个动作,艺术家在描绘他在观看的对象时,书写的动作发生的那一刻,他实际上是盲目的,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描绘的只能是先前所看见东西的记忆。这样,“写生”这一在此时发生的书写本质上就是废墟似记忆痕迹的碎片,它是经验和记忆本身。
刘小东最近的创作则是通过一些规模很大的写生计划将他的绘画过程推向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宏大-他最近的《温床》(三峡和泰国的写生)及为蔡国强策划的金门“碉堡美术馆”开幕展做创作的《十八罗汉》,则是通过多画幅重叠和展开的组织而成为一种过程细致的绘画实践。这三组作品中的人和事件似乎很容易让人想到政治的、人性的寓意和叙事性解释和多意的阐释。但,对于艺术家刘小东来说,让绘画面对障碍,面对生命的不通,面对矛盾的人性,面对艺术的重新突破和时代的困境(这其实是同一问题),回到了最为基本的材料和问题上,以期激发自己最初的表现力,这是他最基本的问题。那也是说,绘画与我们的生命之间的关系如何?无疑,刘小东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一种节奏,对于生命面对的虚无找到了哀叹和书写的共同理由。
所有的艺术都是探险行为,所以艺术家的工作最终都在于发现,换句话说就是把隐藏的真实清淅地呈现出来。(罗伯特·弗拉哈迪,纪录片大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 于上海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 百年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