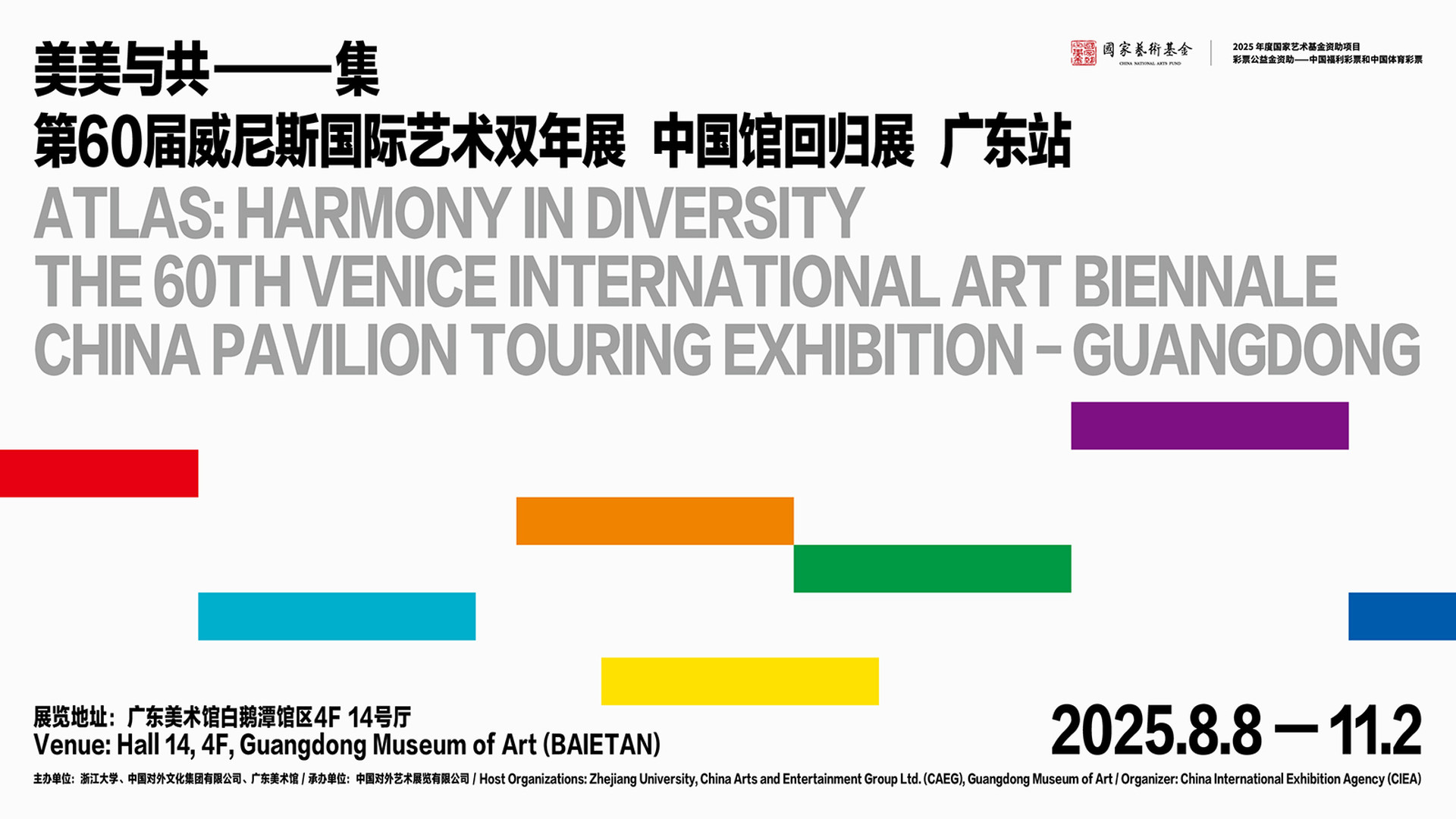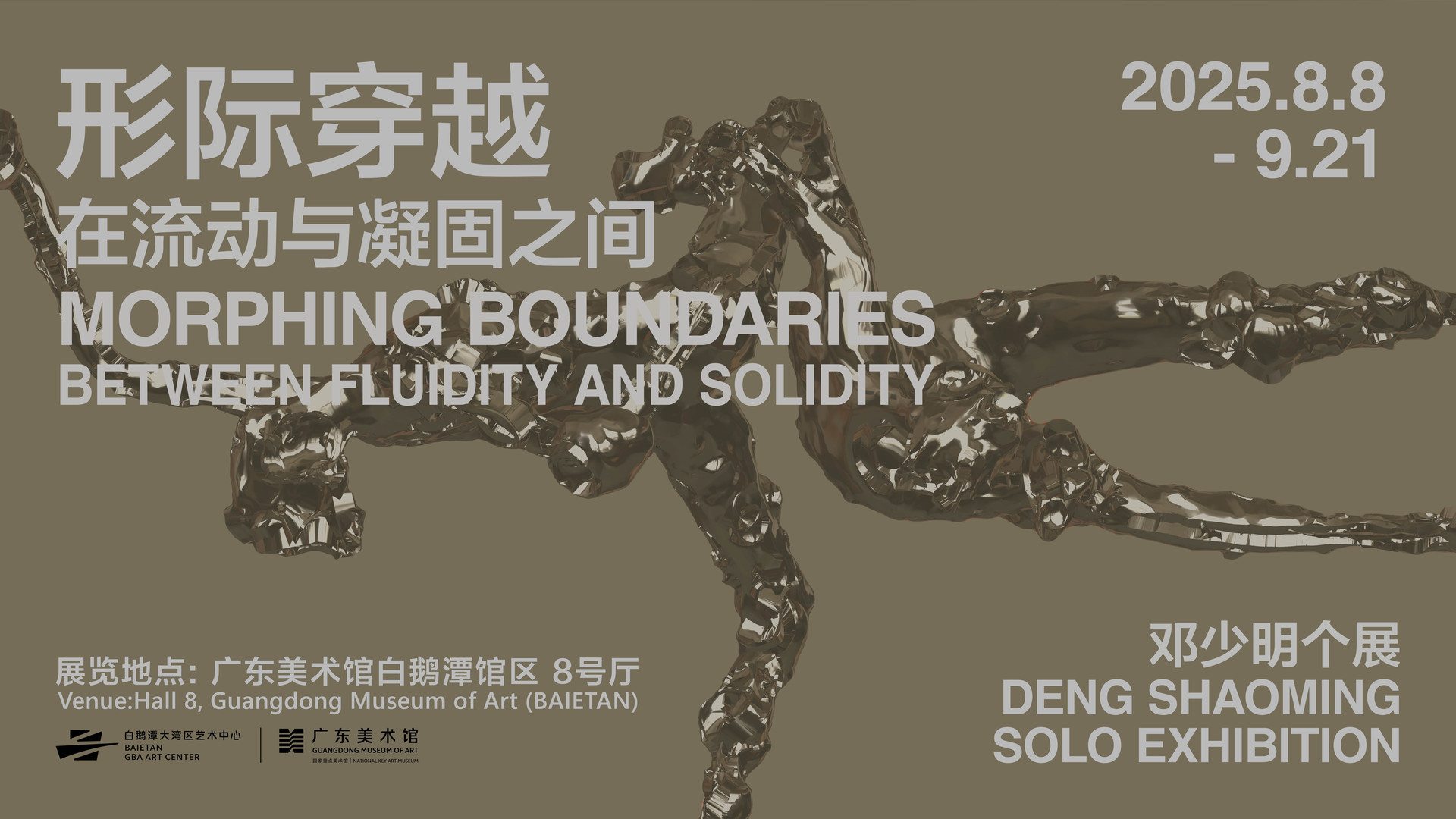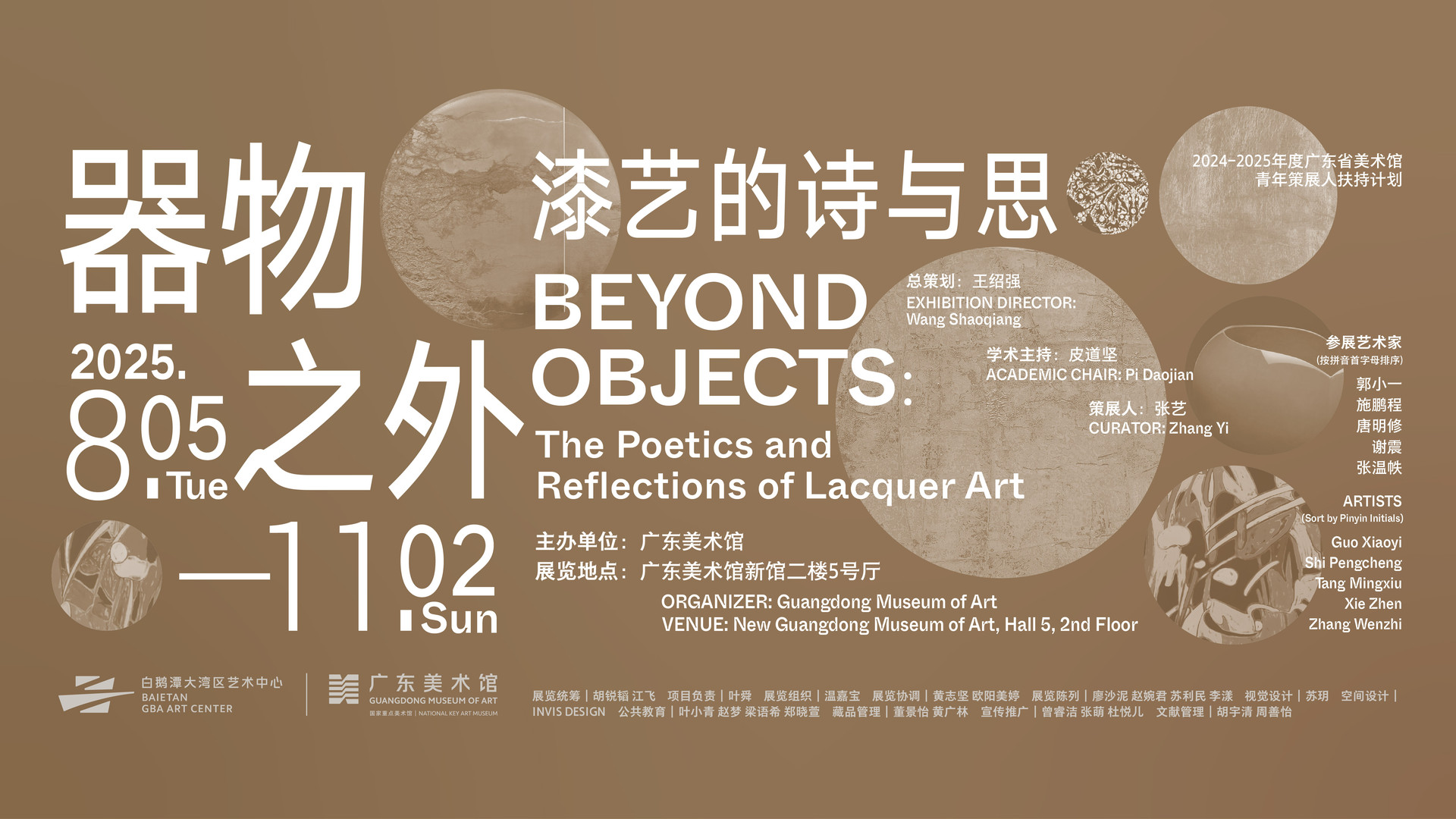【讲座】“见所未见——视觉先行的当代艺术实践” 主题讲座(广美)

讲座丨视觉先行的当代艺术实践
主讲:姜节泓、乔纳森•沃金斯(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主题展策展人)
时间:2012年9月20日19:30
地点:广州美术学院教学大楼0120(昌岗东路校区)
主办:广东美术馆
协办: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处
主讲人简介
姜节泓(中国)
JIANG Jiehong (China)

姜节泓,英国伯明翰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该院中国视觉艺术中心创建人、主任,同时客座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和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姜节泓近年策划的当代艺术展览有《关系 I》(广州:广东美术馆,2011);《关系 II》(北京:今日美术馆,2011)、《没有记忆的时代》和《我变故我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0)、《天使的传说》(伦敦:红楼基金会,2009)、以及《集体形象》(曼城:华人艺术中心;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7)。近年的英文书著包括《负担或遗赠: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到当代艺术》(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革命在继续:来自中国的新艺术》(伦敦:蓝灯书屋与萨奇画廊,2008)和《红:中国的文化革命》(伦敦:蓝灯书屋,2010),以及中文书著《十年曝光: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当代影像》和《关系:与十二位艺术家的书信集》(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
乔纳森•沃金斯(英国)
Jonathan Watkins (UK)

乔纳森•沃金斯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一直担任英国Ikon美术馆馆长。在此之前他曾任伦敦Chisenhale美术馆(1990-95)和Serpentine美术馆策展人(1995-97)。
沃金斯曾出任“第十一届悉尼双年展”(1998)艺术总监。他所策划和合作策划的主要展览还包括:《日常》 (都灵,1999),《第四十七届威尼斯双年展:Europarte》(1997),《欧洲米兰》(米兰,2000),《米兰三年展》(2000),《生活的事实:日本当代艺术展》(伦敦,2001),《泰特三年展:如此岁月》(伦敦,2003),《第六届上海双年展:超设计》(2006),《第八届沙迦双年展:静止生活》(2007),《巴勒斯坦双年展》(2007)。目前他正在合作策划《第二届今日文献展》(北京,2010)。沃金斯近年也撰写并出版了大量关于当代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文字,包括 Giuseppe PENONE、Martin CREED、Semyon FAIBISOVICH、Noguchi RIKA、Caro NIEDERER、Cornelia PARKER、河原温和杨振中等。
录音整理:莫凯琦 / 校对:叶小青
姜节泓:
我跟我的搭档乔纳森·沃金斯,一起策划了这次三年展的主题展。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次展览和我们的理念,我会先花5-10分钟介绍这个展览的框架,然后我们再各介绍8-9个艺术家。
这个展览的英文名称叫the Unseen,直译过来就是“看不见的东西”。我确定这个展览主题之后,一直在考虑中文怎么翻译比较好,因为直译过来并不是那么好听。我记得第一次尝试翻译它的时候,把它译成了“未见之事”。但是,我又觉得不太对,这个译名过于文绉绉,不像一个展览的题目。
后来,有人提醒我,说可以叫“视觉之外”。这个名字就很有展览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视觉之外”还是有点偏了,与“未见”的含义不一样。我特别想保留“未见”这个词。到2010年的时候,我才想到“见所未见”这个词。这个词并不是直译,它对应的英文应该是to see the unseen,去看没有看过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翻译比较符合我们对展览主题的理解,就确定下来了。主题确定之后,我们就开始与各自推荐的艺术家交流,看看哪些艺术家比较适合放在这个策展框架里面来进行讨论。
这次三年展的主题展与以往的展览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届的广州三年展以回顾中国实验艺术为主题;第二届的主题是“珠江三角洲”,也是与中国有关,与地域性有关的展览;第三届是以“后殖民”为主题,也是有一个文化地域性倾向的展览。相对前三届而言,我们这次展览,可以说是一个“最不中国”的展览。我想,其实这个展览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局限,在任何文化、国度、地域中,都会有和未见有关的故事和想象。这个主题由自己独特的空间特色,在时间上也特别有意思。我和乔纳森合作时,一直在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这个展览没有时间限制。无论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一千年前,都可以办这个展览,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未见。因此,未见是一个接近永恒的主题,即使在50年、500年后,仍然会有未见相关的东西存在。因此,大家去看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既选择了很老的艺术家,也选择了特别年轻的艺术家,甚至还有已经去世的艺术家。他们都与未见有关。
这个展览不仅跨地域、时间,还跨学科,因为“未见”太有可能跨界了。比如说声音,我们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声音,因为声音不是靠视觉来感知的,要靠听觉;比如说风,谁都没亲眼见过风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电磁波,一个物理概念,也是没人亲眼见过它的样子。我们这次展览中有选择科学家,这位科学家用视觉的方式,记录了科学的内容;也有选音乐家,因为他也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呈现了未见的东西。因此,我们这个题目里,确实包含了许多跨界的可能。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题目一直吸引我的地方。
对于这个题目,我还想说一下它的简单之处。“见所未见”,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题目很朴素,并不像那些专用的词汇,必须有研究经历的人才能读懂。我们选择的这个题目,不但研究生和教授能读懂,街上卖菜的老太太也能读懂。策展人不需要解释,每个人都有对“未见”诠释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看,这个题目很民主。
展览的框架大致如此,接下来,先请我的搭档乔纳森介绍他选择的一些艺术家。
乔纳森:
大家好!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三年展“见所未见”中,我所负责的一些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在我接到姜教授的邀请我担任本次三年展的策展人的消息时,我觉得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根本无法抗拒。在我这么长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可见与不可见的矛盾性是怎样解决或共存?“见所未见”这个主题,正是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些入选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国,不同时代。我希望能通过对这些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绍,为大家提供理解“见所未见”这一主题的不同角度。


Michael CRAIG-MARTIN (Ireland / UK), An Oak Tree, 1973
说到“见所未见”,我立刻想到一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英国人克莱格·马丁。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艺术作品,名为《一棵橡树》。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到,有一个玻璃水杯放在玻璃架子的上面,水杯当中大概有半杯水。那在它的左下角,是一段访谈文字。其实,这段访谈是艺术家自己采访自己,通过对话我们可以读出:这位艺术家坚持认定这杯水就是一棵橡树。艺术家还强调了一点:这杯水并不是一棵橡树的替代符号,也非具体形象,它就是树本身。艺术家还认为,人们并不是由于被催眠了而认为它是一棵橡树,它本身就是一棵橡树。其实,我对他认为这东西是水杯还是橡树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事,艺术家如何把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日常生活用品转换为一件艺术品。在这件作品中,我看到有一种信仰或信念的力量,使得艺术家得以把一件物品想象或投射成另一件物品,使它成为一件艺术品。这跟宗教信仰很相似。用一个更现实的角度看待艺术,这不仅是我自己本身这么想,艺术家也是这样想的。艺术家希望大家平时能多用眼睛去观察我们周围,发现有哪些是有艺术性的造型或作品。我相信,艺术家本身也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信念:艺术与我们日常生活是分不开的。

Giuseppe PENONE (Italy), Rovesciare i propri occhi, 1970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意大利的著名艺术家,朱塞佩·皮诺内。这张图片里的人就是艺术家本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他的眼睛。我们常说,眼睛是人的灵魂的窗户。仔细看,你会发现艺术家用一双带有镜面的隐形眼镜,把他的这扇窗口给关上了。所以,你往他的眼睛里看,看到的却是他能看到的外部世界。这位艺术家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以及眼睛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在这一件作品里,隐形眼镜反射出整个世界,艺术家想传达给这样的观点: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体验本身。

Ann Veronica JANSSENS (Belgium), Phosphènes
刚刚为大家介绍的两件作品,都探讨了人如何与外界打交道。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比利时艺术家所展现的,是如何与自己打交道。这件艺术品是由安·维罗妮卡·詹森斯创作,当大家走进三年展的展厅,马上就会看到这件艺术品。这是一件装置艺术,做起来也并不难,它暗示观众模仿画面上的人物,闭上双眼,再用手指按着眼球。倘若你能按上5秒钟,就会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变换的亮光和色彩。这件作品吸引了我,不仅是它呼应了“见所未见”这个主题和关注了我们的眼睛。它在进一步探讨,我们平时是在运用不同的感官方式,来感知世界和艺术。艺术家利用了一个生物学的现象。在光谱里,人类的眼睛能感受到的波长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能借用世界上不同事物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我们能看到的世界一定是各不相同的。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取决于许多因素的,包括我们的思维方式、生存环境,等等。这和我之前的一些体验很相似,通过这件作品,我得出一点结论: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紧密关联。

乔纳森·西佩,超慢速装车,装置,2012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美国艺术家乔纳森·西佩。他的作品有很多,在这里,我只为大家举其中一件作为例子。他的艺术创作的核心主旨就是一个字:“慢”。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发生的太快或太慢了,导致我们常常忽视了它们的存在。在这次广州三年展中,西佩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撞车”,正是体现了一个“慢”字。我们都知道,撞车通常都发生得很快,很突然,但艺术家在这里就一反常态,用“慢”来呈现“快”。当三年展开幕的时候,你在广东美术馆会看到两辆车头对头,像亲吻在一起;而你在展览中段再去看时,这两辆车已经有一些摩擦和碰撞了;到了展览快要结束的时候再看,就会发现尽管这两辆车的相撞发生得很缓慢,但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西佩已经在广州寻找这两辆车,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希望找不同的车型,看一下那种会更有意思。现在我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最后激发了他的灵感的,是两辆日本牌子的小轿车。

格拉汉姆·古辛,看不到的电影,2012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名英国的艺术家格拉汉姆·古辛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为“看不到的电影”。这个作品看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以一个9*12的黑色屏幕来模拟电影院里的大屏幕。作品想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时常会因为没有机会或办法去看某些东西,而错过了它。为什么说是“看不到的电影”呢?原来,艺术家把那一场电影的所有门票都买了,其他人买不到票,就没办法进去看电影。作品中只有一句话:“这场电影的电影票都已卖光。”这是因为被遮蔽了,而无法被看见。

雀瓦·裴格兰,敞开的飞机棚/Cactus Flats NV/距离18公里/时间上午10:04,2007
下面是一位美国艺术家,雀瓦·裴格兰。他的作品是通过高倍望远镜和摄像机照出来的,拍摄的对象都是我们平时不知道或看不见的地方。这些地方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会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军事基地或国家需要对公众保密的地方。艺术家在一个荒漠中照到一个机场,但我们在普通卫星照片上是看不到这个地方的,因为这里被人为屏蔽了。从艺术家拍到的照片上看,这个地方虽然看上去很普通,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生化武器基地。维基解密揭示了美国存在许多这样的地方,其实,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多得是。总有一些原因,会导致看不见的结果。比如在这次广州三年展中,有两位挪威艺术家因故不能到来。对于大家来说,这两位艺术家的缺席也是属于未见现象的范畴。

这个作品是来自英国艺术家科妮莉亚•帕克,它并不会在这次展览中展出。但在这次展览中将展出的作品,其的主旨是与图中的作品一样的:除了我们眼见的东西外,还有更多我们平时看不见的、更基础的东西存在。帕克对纪念碑式的艺术品非常感兴趣。纪念碑在许多地方都属于地标性建筑,是吸引游客的东西。而在这个作品中出现的泥土,就是来自意大利的著名建筑物——比萨斜塔。为了防止比萨斜塔继续倾斜,人们挖走了一些泥土,以保持塔身的平衡。帕克从开挖现场把这些泥土带回来,并用绳子穿起来,悬挂在空中。艺术家想传递什么呢?我想,她想说:我们的潜意识在想什么,有可能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究其原因,比萨斜塔是因重力而不断倾斜,重力是摧毁它的罪魁祸首。而艺术家选择用绳子把泥土吊起来悬空,仿佛脱离了重力的吸引。这不正是一种抵抗重力的方式么?
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几个案例都是一些心理上和潜意识上的探索,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们怎样看待周围的现象。

Tim JOHNSON (Australia), Walk Through , 2009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的艺术家蒂姆·约翰森,他的作品中融合了宗教和精神世界。这位艺术家对佛教特别感兴趣,也经常思考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他的作品也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由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约翰森很容易接触到澳大利亚的土著艺术,对土著绘画更是特别感兴趣。这些画作通常反映了土著人对大自然的看法和想法,也包含了他们部落的历史。约翰森使用了一种梦境般的形式来表现宗教的元素,这也与之前为大家介绍的《一棵橡树》有着相似之处。在土著文化里面,人们所看到的并不光是物体本身,而是物体更深远更内在的东西。

植田陆雄,风之画,2002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日本艺术家植田陆雄,他运用风作画。他把纸固定在一个地方,再把笔绑在一个物体上面,当物体随风而动的时候,就可以带动笔在纸上画画了。植田没有在精神层面去追问大自然是什么东西,反而运用了最原始、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大自然是非常伟大的。
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反复诉说关于“看不见”的主题。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我们看见,但又存在许多无法为我们所见的东西。重力、电磁场、风,这些东西都没有实体,不能被看见。这些话题,都回到我们讲座最初,姜教授给大家讲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我们是知道它的存在,却又看不见的。”希望大家能亲自到展厅去,从这些艺术家和作品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姜节泓:
我们在做这个展览时,常常会反过来想,“眼见为实”这句话的不可信的一面。

菲利斯·比亚图,广州古城摄影系列·夫子庙,1860年
我们这次展览中的许多“作者”并不是艺术家。比如菲利斯·比亚图,他是一位跟随军队摄影的摄影师。在1860年,他来到广州,拍了一套广州的照片。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把这组照片也放在“见所未见”这个话题下呢?我是这么考虑得:这组照片里所拍到的广州,早就看不见了。借助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反思艺术本身。什么是艺术?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滑稽与荒诞,让比亚图拍下的这些文献性的东西变成了具有艺术性的东西。过去是我们未见的。对一个城市来说,飞速的城市化建设让我们曾经熟悉的城市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不断变迁,最后,我们发现自己生存在一个没有文化秩序的空间里面。过去的东西,失去了就回不来了。

LEUNG Chi Wo (China Hong Kong), Pun Lun’s Snowy Hong Kong, installation, 2012
这是香港艺术家梁志和在2012年创作的作品,这件作品也与看不见的过去相关。艺术家在作品中记叙了一个事实:在1893年的香港曾经下过一场雪。地处亚热带的广州都从未下过雪,但艺术家说在1893年的香港下过一场雪,你相信吗?你们没见过,所以不信,对吗?这是1893年的《中国邮报》上有一段文字:“在1893年,这样一个亚热带地区下了一场雪。”然后有一位摄影师号称拍到了传说中的这场雪,只是照片已经找不到了。而到现在,见过这场雪的人大都死去,这场雪就变成了一个传奇。真假难辨。艺术家恰恰是借用了这个不确定的事实创作了这件装置。

隋建国,一立方米绝对黑暗,2012
这是隋建国的作品,它有个很酷的中文名字叫“一立方米绝对黑暗”。当你想要展示一幅画的时候,展示任何内容的时候都能展示,当你要展示一个绝对黑暗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展示呢?艺术家说这里面是一立方米的黑暗,你们信吗?里面很可能不是黑暗,是别的什么东西,藏了一个秘密,只是我们都看不见。眼前的这个铁盒子是用16毫米的钢板焊成的,如果没有特殊的方法和工具,我们根本打不开它。不打开它,怎么确定里面装的是不是黑暗呢?有趣的是,假使你想象自己能进入了这个盒子,能够到里面去直面黑暗。但,黑暗对我们而言还是未见的。所以说,这件作品里面形成了好几层思考:人的感官能力是如此有限,我们的想象能在何处安家?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所探讨的问题:想象力。在艺术上,这种想象力是通过视觉来完成。当你看不见一个东西的时候,也正是想象力最容易生效的时候。越是看不见,越是想看见。

涂维政,生日快乐,2012
接下来的这件作品,也是有关视觉想象力的作品。台湾艺术家涂维政把盲文打在一个铜片上,变成一个发音盒装置的一部分,让盲文的诗句能变成美妙的音乐。我很喜欢这种转换,于是邀请他为广州三年展做一个类似的作品。他与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的同事们一起讨论,几番周折找到了四位盲童来书写愿望。他们每个人都许下了一个生日愿望,涂维政再用老办法把这个愿望转换为盲文,置入到四个装置中,演奏出四段美妙的音乐。回过头想,让人感动的正是艺术家的这种关注力。艺术家不需要很伟大,他只需要转换一点小小的东西,也许就能给世界一个改变的可能。

咸京我,抽象编织—摩丝密码,2012
咸京我是我很喜欢的一位韩国艺术家,她的作品在运输途中出了许多麻烦。我是在策展研究过程中发现她的。她在报纸上收集一些很普通的新闻消息,如:奥巴马当总统、地铁出事故,等等,再把这些信息设计到抽象的绘画里去。她通过一个中国的中介人,把这个设计方案转送到韩国的刺绣厂里面,让刺绣工人一针一针地把这些信息刺绣出来。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形成了特别有意思的“距离”和“速度”关系。对我们而言,获取信息实在是太简单了,网上一查,马上就跳出一大堆信息来。但对于朝鲜人,他们却要(通过刺绣的方式)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读同样一条新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现实,通过时间,艺术家探讨了借与被借,看与被看的权利问题。

陆扬,绝对零度之上的残酷电磁波,2012
而来自中国的年轻艺术家陆扬,则在讲关于“眼见为实”的问题。她通过一台红外线拍摄仪,来看一个个的人物。这个人有某一个假肢或某一个假牙,红外线摄像仪就能很敏锐的捕捉到它,高温的部分呈现红色,低温的部分呈现蓝色。她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橡皮筋套在手指头上,当这个指头彻底失血的时候,在红外线拍摄仪上就会逐渐变成蓝色,最终与背景融为一体。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安装了一只假腿,只要我走路够稳,普通人不一定能看出假腿来。但在红外线影像中,你就能看到假腿的存在。这一台精密的仪器,给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世界。

伯明翰广告牌计划,2012
这是我们在英国做的一个广告牌艺术项目,其中包括了没顶公司的作品。这件作品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像宣传品,又像艺术品。其实,它是在探讨原作的问题。图中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装置,一匹马,艺术家拍照之后,就把装置销毁掉,只剩下照片。因此,当这个装置消失之后,影像文献就替代了它,成为了原作。这跟徐震如何变成没顶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艺术家被一个公司替代,公司也就成了艺术家的真身,使得艺术家永远在展览中缺席。我认为,这是一个挺有趣的概念。

庄辉,1995年在三峡打孔时留下的痕迹,1995
庄辉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大家都知道长江三峡。除了地理学家,现在还有许多当代艺术家都在不断的反思长江三峡给中国的自然环境、人文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庄辉的这件作品主要采用了摄影的手段来呈现思考的过程。就我所知,庄辉的作品可能是最早的关于长江三峡的艺术品了,它几乎跟三峡工程同时开始。三峡工程是1994年启动的,庄辉在1995年4月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艺术项目。这个项目非常简单,艺术家沿着三峡的长江水岸,在地表上打孔,他打了几百个40-50厘米深的孔。每次打好一个洞,他就为这个洞拍一张照片。拍完照片之后,庄辉也没有告诉大家他做了这个东西,直到2007年工程完工了,他才拿出来。这件作品的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庄辉是一个很有预见性和敏感度的艺术家,早在工程动工的时候,他就有所预见,开始实施自己的艺术计划。这些洞在大坝建成之后全部被淹没,本体没有了,照片也就成为了原作。经历了这些年的变迁之后,这些洞变成了很奇怪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们发生过,但是永远见不到。
最后,我要讲的是一系列作品:正佳广场计划。大家可以看到一张正佳广场的照片,却没有一件艺术品在上面。为什么呢?正佳广场计划只能邀请大家亲自去看了,我不想提前剧透给大家。如果一个大型购物广告邀请你做个艺术品放在里面,你会如何做呢?做个雕塑?无论你做多大的雕塑,放进这个广场之后,都会被它的空间吃掉。大家都去过购物广场,知道购物广场的氛围。购物广场的视觉力量太大了!当我接到这个项目时,感觉到特别难,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如何做作品?然后,我就尝试去跟艺术家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当艺术家们看到正佳广场的照片时,都惊讶了。
我与他们开会讨论时,大家突然发现,作品放进去都会被吃掉。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展作品,而是去藏作品。面对特别强大的敌人时,我们可以选择不与它硬碰硬,我们可以换个法子来与它周旋。艺术与日常生活短兵相接,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到底,正佳广场里面的哪些东西是艺术品,哪些不是呢?这些棕榈树是不是艺术品呢?我相信,你们到了现场也很容易找错作品,因为生活实在太有创作力了!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生活与艺术之间,有没有距离?要是有距离的话,能有多少距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