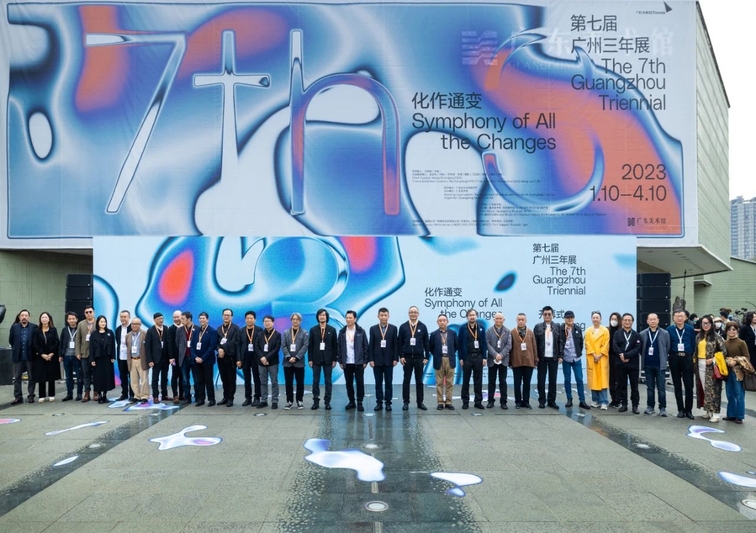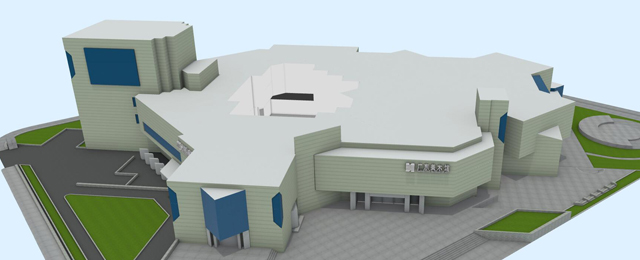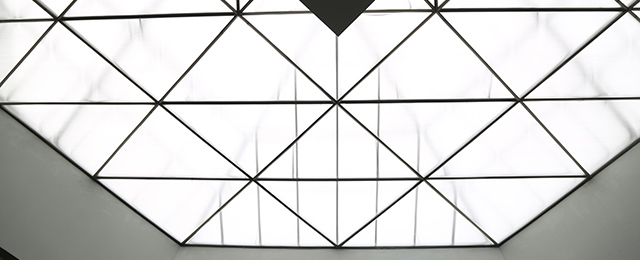光的现代性《南方都市报》
录入时间: 2014-01-16

《海滨》 乌戈·弗鲁米亚尼

《高安蒂尼亚诺》 拉法纳罗·坎博奇

《阿尔诺河河岸》 伽利略·基尼

《白帆船》 弗朗切斯科·保罗·米凯蒂

《草原牧场》 乔万尼·法托里

《行军图》 路易斯·比安奇
策展人:杨小彦
就人类进步发展史来说,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科学知识和科技发明爆炸的年代,绝大部分影响今天人类生活的科技,都是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中涌现的。随处泛滥的摄影术,是在十九世纪晚期注册专利的;改变人类作息习惯的照明灯,是在二十世纪初发明的;今天成为环保灾难的汽车,也是出现在这样一个年代;而从电报、电话到电视,也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明并迅速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用品。
著名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代表性的专著《艺术与错觉》,讨论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点彩派的西方艺术发展,试图从图像学和心理辨识的角度,回答艺术何以有一部历史的问题。他开篇选的艺术家,是十九世纪初的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这当然是这个伟大的人文学者的历史观的一种体现。在他看来,发生在爆炸年代的艺术实验,无疑是从一个科学目标开始的,那就是寻找“物理般的眼睛”。这场今天被称为“印象主义”艺术运动,从贡氏的“错觉主义”角度看,终结在修拉的“点彩派”是合乎情理的,尽管还有三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是塞尚、高更和凡·高,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三个风格不尽相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发展方向。但是,寻找“物理般的眼睛”的确在“点彩派”的追求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并让科学与艺术达到了某种令人惊讶的一致。
“物理般的眼睛”指的是对光的理解与描绘。长期以来,由于某种褊狭的理解,中国艺术界有不少人以为,西方艺术是“写实”的产物,“写实主义”可以概括西方的“本质”。殊不知用“写实”理解西方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偏见。如果稍微了解西方艺术发展的一般状况,我们就能认识到,对光的捕捉与理解,才是构成过去一百年间西方艺术变化的核心动力。在这里,“物理般的眼睛”除了涉及到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之外,同时又与西方的另一个传统有关,那就是对光的认知。在这一传统看来,光才是物象呈现的根源。也就是说,正是“上帝之光”才照亮了万物,并让艺术家有事可做。终结了西方艺术对光的探索的修拉对此有过清醒的总结,在他看来,他的绘画只是恰当地证实了物理学的光谱分析。所以,修拉的结论很清楚:艺术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或者更彻底地说,艺术就是科学。
今天我们可以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批评修拉的观点,并指出他的说法包含了某种“取消艺术”的可怕倾向。但是,历史的意义正在于,终结者同时也必然是开拓者。如果没有“点彩派”,没有修拉的极端表现,艺术方向真的会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发生逆转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恰恰是修拉提醒了我们,在那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时代,“光”就是现代主义的早期目标。这提醒我们,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深入了解从牛顿古典物理学向爱因斯坦现代物理学的转变过程,我们就一定能体验其中燃烧的激情,那可绝对不亚于我们对于艺术的崇敬与热爱。
在这里,“物理般的眼睛”的意思是,如何画出真实的外光效果,是考验我们眼睛观察世界的一道门坎。正是在这一点上,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首先表现了他的非凡勇气,那就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光,他携带画箱出外写生,坚持面对自然,而不是关在画室里,面对画布和古典作品。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他在十九世纪中叶画出了《干草车》,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几年前,当我站在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面对康斯太勃尔的《干草车》,我无法从眼前的作品中体验出当年人们对于光的特殊爱好,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受到整个印象主义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的洗礼,眼前印象不可能复现当年情景。我只能想象,1864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当年轻的莫奈站在这幅从英伦过来的著名作品前,他是如何地惊讶,又是如何地激动。新一轮对外光的追求与描绘,正是从这个年轻人天才般的眼睛重新开始并达至惊人效果的。如果把1874年作为印象主义正式登场的开始,那么,从艺术史的角度看,那也是现代主义正式登场的开始。印象主义不仅仅是一场外光派的运动,印象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场运动。这是迄今为止艺术史的正宗观点。否则,我们不
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场发端于法国的艺术运动,会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方,然后在二十世纪蔓延到东方乃至全世界。我在一本描述从1874年到1940年间印象主义全球扩散的专著中,惊讶地发现,远东的徐悲鸿,这个曾经尖锐地反对马蒂斯的中国写实主义画家,也被纳入到印象主义运动之中,而赫然列名其上。
显然,光不仅是光那么简单。光代表了一种对现代性的追求。光就是现代性的一种表征。在一个时期,光甚至是现代性的唯一表征。
以上就是我徜徉在意大利博罗尼亚一个关于托斯纳卡地区与印象主义运动同时期的小型油画展的第一观感。我感慨印象主义的那种独特魅力,从法国扩张,迅速覆盖了欧洲其他地区,并与这些差异极大的地区的本土趣味结合,变异出奇特的画面风格,而其内核又绝对不偏离对于光的强烈爱好与持续描绘。
这是一个小型的油画展。画家当中,出生最早的是1825年的来自利沃诺的乔万尼·法托里,他画于1880年前后的《草原牧场》,依稀可见康斯太勃尔式的那种自然风格。而稍晚出生在米兰的路易斯·比安奇(1827),他画于1865年前后的《行军图》,则仍然呈现了一种后期学院派的基本特色,慎重而小心地吸取某种外光效果,是印象主义运动之前的风格。1854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凯撒·齐亚尼,显然在外光效果上就超越了路易斯·比安奇,虽然他还是以人物为母题,造型上表现了学院派的扎实功底。有意思的是,恺撒·齐亚尼画于1880年前后和1895年的两幅肖像,典型地再现了一种混合学院派与外光效果的奇特组合,形象地告诉我们,在那个现代主义运动早期,一种新的观念是如何在旧有惯习的框架内运行的。活跃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乔万尼·科万奇基,就表现了现代主义成熟时期的趣味。创作于战后的1940年前后的《洗浴的人》,是这一次画展中的精品,创作手法是那种经过二战以前现代主义艺术洗礼之后的典型效果,成熟的外光色调,略带立体主义倾向的造型,以及多少平面化的构成因素,都告诉我们,他所关注的目标,已经不是光线本身,而是由光所组合的审美可能。有意思的是,他创作于1931年的《白花瓶》,具有一种回归的风格表象,色调沉稳,有一种重温外光运动之前的情感依恋,但造型上却明显吸收了立体主义的成果,同时又把这一分裂物象的手法糅和进统一的构成之中。我怀疑这样一种审美,是否和早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整体气氛有某种内在关联?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猜测,并不代表对画家风格的正确研究。1881年出生在卡拉拉的阿图罗·达兹,他创作于1937年的《雨后》引起了我的关注,那种清闲干净的风格,对色调的统一处理,摆脱了单纯外光的追求以及印象主义运动的表面干扰,呈现了一种意大利式的独特趣味,让我不期然地想起著名的莫兰迪,他在其景观描绘中所表现的对于自然的主观感受,在阿图罗·达兹的这幅小型画作中找到了某种影子。我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我直观地认为,莫兰迪那种摆脱现代主义表面纠缠的手法,一定在意大利,尤其是托斯纳卡地区,有着比外人想象更为深远的灵感根源。出生在印象主义运动正在兴起的1876年的乌戈·弗鲁米尼亚,他的作品告诉我,他对于这一场运动有着多么强烈的忠诚。他画于二十世纪初期的《海滨》,是用一种典型的莫奈的眼光来创作的,甚至在色调上都让我们不期然地回想起盛期印象主义的那种辉煌样式。同样出生在这一年代的拉法纳罗·坎博奇(出生在1874年,正是“无名艺术家与雕塑家作品展览”,也就是印象主义第一次展览在著名的纳达尔工作室展出的同一年),也表现了他对印象主义的痴迷与向往,他画于1900年前后的《高安蒂尼亚诺》,色调上更进一步,画面微妙颤动的紫色,明确地传达了成熟的印象主义的所有成果,尤其对阴影的处理,如果没有对同类风格的持续探索,很难想象画家能以这样的手法来处理光线。
总之,尽管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型画展,作品七十余件,但其意义却依然不同凡响,形象而有力地证明了一场现代主义运动是如何在不同地区得到的奇特回应,也从旁证明,那种蕴藏在艺术风格之中的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如何具有普遍的价值,否则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并非欧洲文化中心的区域,竟然以一种成熟而坚定的态度,去印证与时代合拍的艺术潮流,去落实一场适应现代趋势的审美革命。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尤其联想到意大利在世界艺术史中的伟大作用,联想到托斯纳卡地区,以及其中心城市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中的重要的引领地位,我们就会明白,一种传统是如何传承、如何变异、如何适应历史与时代的,然后,我们必然要以一种崇敬之心,来面对眼前的油画作品。历史的趣味正凝结在这些小型作品之中,向我们诉说着艺术的荣耀。艺术史一再证明,“光的现代性”是勾勒那个过渡时期的核心主题,这个主题既发生在艺术内部,呈现为观看自然的变革;也发生在整个社会的表面,引领了一场触动人类审美灵魂的革命。展览就是一个明证。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开幕式现场 2025年11月21日,“单凡艺术四十年”展览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