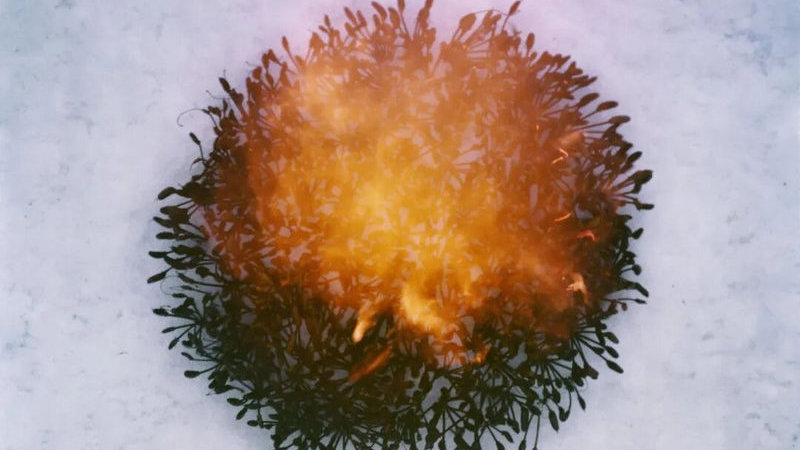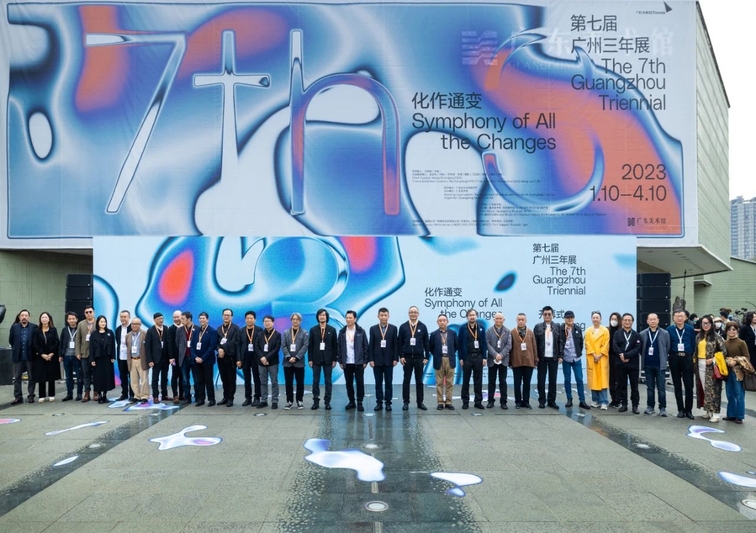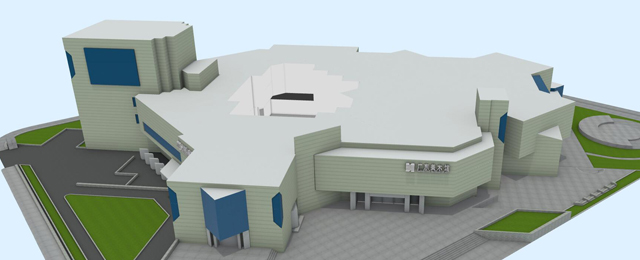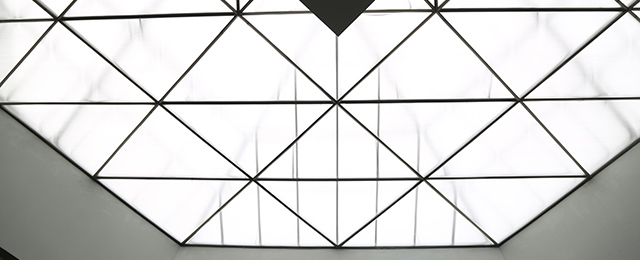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现象:‘后岭南’与广东新水墨”研讨会纪要
录入时间: 2007-10-25
(按语:2002年9月6日,“现象:‘后岭南’与广东新水墨”专题展览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同时举办了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广东美术馆王璜生馆长主持。以下是根据研讨会录音整理的纪要。录音整理方立华,文字整理王嘉。因篇幅关系,有删节。)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策划这次展览的想法。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展览来体现广东新一代的水墨画家的创作状态和精神。因为若干年来,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存在“后岭南”这样一个画派。它能否成为一个画派,我们暂且不谈。但是,至少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这么多年来,也有一些从北方、外地、海外归来的年轻水墨画家,为广东水墨增添一些新的格局,形成了很多种不同的现象。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展览,把这些现象呈现出来。在这过程中,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还是抱着一种充满信心的态度去进行这项工作。那么,这里面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好像说,理论跟不上啦,或者太个体化啦,等等。这些问题在艺术本体方面,好像说个体化问题等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余地。今天,这个展览终于举办了,东西拿出来了,构成了这样一个探讨的平台。通过这个展览,通过大家这么认真地去进行准备这些作品,可以看看我们的工作究竟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从总体上还存在什么问题,或者个体上还存在什么问题?我就做一个简单的开场白。
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这次展览叫做“现象”和“后岭南”,我觉得挺好。最近,我看到一个外国学者谈中国经济状态,他是这样讲的:当我们谈中国的经济状态如何,最好不要去沉迷于统计数字,最好是直接到中国去了解它的市场状态和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他的研究方式是对的,因为研究问题有几种方法。一个是根据别人固有的统计,别人固有的评说,然后再对评说家评说,对统计家做自己的演绎,这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通常说这种方法是认识的一种方法或者是方法论的方法。
关于“后岭南派”的问题,早在1993年,一班人已经聚在一块了,已经开始组织后岭南派的第一回展、第二回展、第三回展,而且在《江苏画刊》或者全国的一些报刊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有一种倾向是很明显的:当时内地的有些画,洋气十足,适应洋人的猎奇心理,往往就是那些穿着红兜兜的小脚女人,半裸体的那种,迎合洋人的殖民心态的东西。而在广东,当时黄一瀚、李劲堃、陈新华、苏百钧等经常聚集在一起,探讨怎样去用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来表达。后来他们团结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反映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一种新的文化感受,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至于有人说,后岭南派是不是一定有共同的东西?画得都差不多,有共同的追求,才能形成一个派别?我想在美术史上,比如说后印象派,他们只是对印象派的某些客观主义倾向、自然主义倾向,过分重视光线、空气这种表现的一种反驳。然而凡高和高更,高更和塞尚,塞尚和凡高,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三个人画得不像,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派了。他们都从印象派来,又不同于印象派,他们强化了某些被印象派忽视的东西。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在艺术史上站住脚了。我想后岭南有这个特点,他不同于岭南派,但是他们又从岭南派中来,他们又吸取了岭南派一些宝贵的东西。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对岭南派积极精神的继承,对某些泛岭南派的消极因素的中断。所以,他们提出了“后岭南派”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后岭南派崛起》中谈了。我就谈到这里,谢谢!
陈映欣(广东美术馆研究部策划人):
其实,我的看法在我的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我的发言权还是太小。我在那篇文章中,也只是谈到一种现象跟目前的各种看法。我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看法,关于画要怎么画,接下来要怎么走,每个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策划人和主持人的角色。画要怎么画?接下来要怎么画?还是要听听艺术家们的说法。
皮道坚(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今年五月份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一个中国画的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画百年的命运和前途”。去的有中国大陆的、有台湾的、有海外的华人艺术家,也有一些策展人。会议上的交锋非常激烈,主要是关注中国水墨,它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它未来的走向等。
回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后岭南和广东新水墨”的展览,大画不少,强烈的画不少,鲜艳的画也不少,是不是说我们的作品里边就没有问题呢?就这样可以推向世界呢?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不是画面大了,就证明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画面颜色鲜艳了,是不是画面图式醒目了,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今天这个展览还是出我意料的,我没有想到这次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作品,而且其中有一些确实是很好的作品。展览的题目是“后岭南”,我不把“后岭南”看成一种画派,我把后岭南看成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正好是一种百年的巡回。岭南派崛起的时候,当时也正是处在中国画革新的形势之下。岭南画派给中国现代画史带来了中国画革新的一个潮流,开风气之先。岭南派立足于表达身边发生的新事物和他们对新事物的感受;岭南派对外部文化也是开放的,对100年来的中国画都是有意义的。历史走过这一段,我们再来谈这个“后岭南”,应该是这样一种精神。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画派的概念在逐渐地淡化。艺术创造归根结蒂还是非常个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定要把后岭南作为一个画派提出来?在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讨论的。
第三,我从这个展览里边看到了广东文化的希望!刚才我在看李正天的那篇文章,前面引了傅抱石的一句话吧?是1937年写的,他说他觉得中国画要有希望啊,希望要在珠江流域。现在,他那个预言实现了。因为这个展览确实体现了很大的开放度和很大的包容量。他们有人开玩笑说有新客家,这个展览里面有新客家,就是有从外地来的。另外也有广东直接延续了岭南派的文脉的。形成了我们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的面貌,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研究员):
刚才皮老师说的那个杜博真,上次在上海开会时见过,非常能干!她是海姆博物馆的副馆长,她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画非常有热情。她所说的东西,可能我们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画的变化没纳入她的视野吧!以前这么大的画她也没见过。所以她提出那个见解我估计是有根据的。
另外一个话题,皮老师刚才讲了岭南派和后岭南派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而且他类似的意见,在他之前我写的文章里面我也表达过。记得那时候是应了黄小敏的小品而写的一篇文章,在《粤海风》发表过,题目叫《一个新的话题岭南派的以后的一个后岭南派》,在发表的时候题目给我改过了,但是内容没有改。
我非常同意皮老师的意见,岭南派到底是不是要用一个画派这种概念来指称它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正像岭南派一样,主要是一个美术史学的概念。在高剑父生活的时代,岭南派的领袖高剑父,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创一个画派这样的愿望。而且,现在被我们指称为岭南画派的画家,在民国年间,他们之所以会引人注目,在历史上获得地位,主要是在冲破传统倾向方面的努力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是说他们怎样形成一个完善的画派,或者说促进了某个能够领导画坛时尚的领袖。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又热衷于谈后岭南画派呢?关于它的背景我在文章里边也有讲过。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岭南画派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它不但在广东地区到处搞这样的展览,而且有一大班的画家自认为是岭南画派。包括广东文化政策里面也有强调:发展岭南画派,包括发展岭南派的音乐,就是发展岭南文化。这样就在理论上造成一种误解,特别是有一些热衷于表现的画家,其实用我们的艺术史的观点来看,他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真正有建设意义的贡献,只不过在不断重复某些画家的风格。所以就说,我们这边是热,但是在外界在外头人们对岭南画派的评价是随着这种活动的越来越热火而不断的下降,这是事实。所以在广东,有些有作为的画家,他们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所处的位置,如果再继续打岭南派的旗号,我看他们的前途就是凶吉未卜。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岭南派的“后岭南派”才提出来。
我的理解就是,其中有不少的画家,他并不是说通过后岭南派来形成一个画派。只不过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跟当时社会上不断强调岭南画派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在寻求一种新的发展空间,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这种意义上,我非常认同皮老师所说的。它主要是一种精神,高剑父那个时代的艺术核心的一种精神。当然,我的认识也许无意会给现在一些后岭南派的画家一些影响。但是,我坚持我的这个观点。如果要致力将来的话,就我个人来看,那意味着这个后岭南派的发展是很成问题了。
因为在1940年代,关山月在画坛上能够引人注目他是西北之行以后大家才关注他可是大家如果注意看文献的话,他当时出了两个画册,一个叫做《西北、西南纪行画集》,一个是《南洋写生画集》。前边有徐悲鸿,有庞薰琹写的序,庞薰琹在序里谈到:“我不知道关山月他自己认不认为他自己是岭南画派?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我希望他能够走出这个想法的阴影。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
关于后岭南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在组织展览的时候,也尽量避开所谓“后岭南派”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使用的是“后岭南”与“广东新水墨”这个说法。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就是说“后岭南”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就像我在前言里面写的“现象”是“精神的表征”的提法。
记得1993、1994年前后,他们后岭南派在热火朝天的时候也请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后岭南”是一种文化策略》。我认为,提出“后岭南”这个说法在当时来讲是一种文化策略。也就是说,这群年轻一代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是长期在岭南画派的笼罩之下,要突破这种笼罩而确立他们新的一种地位,同时又借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既借用了他们长期以来在广东受到各方面所肯定的“岭南”这样的称号、这样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荣冠,然后慢慢去转换这种荣耀之间的很微妙的关系。当时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岭南画派是一种艺术革新、艺术革命的一种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广东非常突出的文化精神。
刘子建(深圳大学艺术家):
我就谈我自己的感想。“后岭南”肯定跟我们后来到广东的这些人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广东对我们后来的人确确实实给了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1992年来广东的,批评界对我比较肯定,我的个人风格、个人语言,说我找到一条自己的路。我回头想想,为什么在湖北这么多年没有变化,而到广东以后,发生完全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因为广东给我提供了不一样的内涵。我把广东的美术现状,跟其他几个重要的地方进行比较,确实觉得广东真的有非常大的长处。
现在要谈中国画的话,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北京。现在看起来是浙江,谷文达当初当然是一个例外。但是,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人去掉,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浙美的绘画,我觉得气度是越来越小。北京呢,北京的学院派占了先锋,但同样是他们的气度也越来越小。而回到展厅来看广东的绘画,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我在这些作品面前感到一种很大的气势,这应该是广东的一个特征,可能跟广东一直以来处于改革的前沿很有关系。所以,我想后岭南和岭南有什么关系,倒是觉得笼统称广东新水墨更加强大一些。因为这里有很多我的朋友,大家一起活动,他们的思路不局限在广东。真正要把广东新水墨向全国推广的话,还需要在岭南和后岭南文化上下功夫,要让别人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别人一般认为,广东很有钱,其他方面的评价不太多。
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研究员):
刚才皮老师说的那个杜博真,上次在上海开会时见过,非常能干!她是海姆博物馆的副馆长,她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画非常有热情。她所说的东西,可能我们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画的变化没纳入她的视野吧!以前这么大的画她也没见过。所以她提出那个见解我估计是有根据的。
另外一个话题,皮老师刚才讲了岭南派和后岭南派的关系。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而且他类似的意见,在他之前我写的文章里面我也表达过。记得那时候是应了黄小敏的小品而写的一篇文章,在《粤海风》发表过,题目叫《一个新的话题岭南派的以后的一个后岭南派》,在发表的时候题目给我改过了,但是内容没有改。
我非常同意皮老师的意见,岭南派到底是不是要用一个画派这种概念来指称它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正像岭南派一样,主要是一个美术史学的概念。在高剑父生活的时代,岭南派的领袖高剑父,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创一个画派这样的愿望。而且,现在被我们指称为岭南画派的画家,在民国年间,他们之所以会引人注目,在历史上获得地位,主要是在冲破传统倾向方面的努力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是说他们怎样形成一个完善的画派,或者说促进了某个能够领导画坛时尚的领袖。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又热衷于谈后岭南画派呢?关于它的背景我在文章里边也有讲过。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岭南画派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它不但在广东地区到处搞这样的展览,而且有一大班的画家自认为是岭南画派。包括广东文化政策里面也有强调:发展岭南画派,包括发展岭南派的音乐,就是发展岭南文化。这样就在理论上造成一种误解,特别是有一些热衷于表现的画家,其实用我们的艺术史的观点来看,他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真正有建设意义的贡献,只不过在不断重复某些画家的风格。所以就说,我们这边是热,但是在外界在外头人们对岭南画派的评价是随着这种活动的越来越热火而不断的下降,这是事实。所以在广东,有些有作为的画家,他们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所处的位置,如果再继续打岭南派的旗号,我看他们的前途就是凶吉未卜。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岭南派的“后岭南派”才提出来。
我的理解就是,其中有不少的画家,他并不是说通过后岭南派来形成一个画派。只不过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跟当时社会上不断强调岭南画派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在寻求一种新的发展空间,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这种意义上,我非常认同皮老师所说的。它主要是一种精神,高剑父那个时代的艺术核心的一种精神。当然,我的认识也许无意会给现在一些后岭南派的画家一些影响。但是,我坚持我的这个观点。如果要致力将来的话,就我个人来看,那意味着这个后岭南派的发展是很成问题了。
因为在1940年代,关山月在画坛上能够引人注目他是西北之行以后大家才关注他可是大家如果注意看文献的话,他当时出了两个画册,一个叫做《西北、西南纪行画集》,一个是《南洋写生画集》。前边有徐悲鸿,有庞薰琹写的序,庞薰琹在序里谈到:“我不知道关山月他自己认不认为他自己是岭南画派?如果他有这种想法,我希望他能够走出这个想法的阴影。他虽然是高剑父的学生,但是艺术上流派的倾向是疏忽、压制这个艺术家的魔掌。希望他尽早摆脱这个东西。”我觉得他的讲法是非常中肯的,而且像庞薰琹这种真正接受20世纪现代艺术思想的熏陶的画家才能说出来的话。现在重温他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讲的就是这些。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
关于后岭南这个问题,我们这次在组织展览的时候,也尽量避开所谓“后岭南派”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使用的是“后岭南”与“广东新水墨”这个说法。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就是说“后岭南”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就像我在前言里面写的“现象”是“精神的表征”的提法。
记得1993、1994年前后,他们后岭南派在热火朝天的时候也请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后岭南”是一种文化策略》。我认为,提出“后岭南”这个说法在当时来讲是一种文化策略。也就是说,这群年轻一代艺术家,他们一方面是长期在岭南画派的笼罩之下,要突破这种笼罩而确立他们新的一种地位,同时又借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既借用了他们长期以来在广东受到各方面所肯定的“岭南”这样的称号、这样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荣冠,然后慢慢去转换这种荣耀之间的很微妙的关系。当时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岭南画派是一种艺术革新、艺术革命的一种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广东非常突出的文化精神。
刘子建(深圳大学艺术家):
我就谈我自己的感想。“后岭南”肯定跟我们后来到广东的这些人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广东对我们后来的人确确实实给了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1992年来广东的,批评界对我比较肯定,我的个人风格、个人语言,说我找到一条自己的路。我回头想想,为什么在湖北这么多年没有变化,而到广东以后,发生完全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因为广东给我提供了不一样的内涵。我把广东的美术现状,跟其他几个重要的地方进行比较,确实觉得广东真的有非常大的长处。
现在要谈中国画的话,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北京。现在看起来是浙江,谷文达当初当然是一个例外。但是,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人去掉,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浙美的绘画,我觉得气度是越来越小。北京呢,北京的学院派占了先锋,但同样是他们的气度也越来越小。而回到展厅来看广东的绘画,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我在这些作品面前感到一种很大的气势,这应该是广东的一个特征,可能跟广东一直以来处于改革的前沿很有关系。所以,我想后岭南和岭南有什么关系,倒是觉得笼统称广东新水墨更加强大一些。因为这里有很多我的朋友,大家一起活动,他们的思路不局限在广东。真正要把广东新水墨向全国推广的话,还需要在岭南和后岭南文化上下功夫,要让别人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别人一般认为,广东很有钱,其他方面的评价不太多。
看了这个展览,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外地人不太了解的,而且,在别人的印象中,我们这些外来的,跟广东本土的艺术家还没有被看作一个整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深有体会,我能够画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可以说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画到这个成果,从这点上来说我是很感谢广东的。
鲁 虹(深圳美术馆研究员):
今天很受启发,这个展览办得很好。多元化的格局也显示了很多新的趋向,也需要去研究。就我个人而言,这个课题跟我的研究也有关系,因为我目前对消费文化有研究,所以我对这种趋向比较感兴趣。
后岭南的展览办了四次,这次和前三次不同。其中有几个艺术家,把他们的创作和消费文化挂上钩,这显示了一种新的趋向。像黄一瀚、周涌、方土等,都是蛮好的。
新水墨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1990年代以来到外国办展览,水墨作品总是一种不能很好参与的尴尬局面,它没有很好解决跟当代文化对位的问题。而黄一瀚他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其实,消费文化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地区,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大都市,已经是站在很重要的地位,它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结构,改变了我们驾轻就熟的生活,也产生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我觉得艺术家在创作中敏感切入到消费文化中,也是给水墨文化创作带来一种新的空间,给多元化的格局增加新的品种,这是很好的,这种倾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我就谈这一点。
黄一瀚(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后岭南”画派是在1992年提出和组织起来的,当时来自北方的就只有一个刘子建。为什么我们自始至终不放弃这样一个东西?这里,有我们的一个理由。很多批评家都说要走向西方走向国际,但是,我发现只有关心我们的生存状况,解决在我们本土的东西,才是更宝贵的东西。我们很多理论搞反了,激扬起来就说要走向世界,碰了两下壁就回来说要关心本土。实质上,关心本土就是关心界。
最近南北交流很多,北方画家到南方来,南方画家到北方去,这种差异已经看出来了,看得一清二楚。在广东,既然还有这么样的一群画家,在这样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还抱着后岭南,我想这一定有它的意义,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杨小彦最近编辑了一套美术史,其中谈到广东的时候,就谈到岭南画派和后岭南画派。他把这两个画派归为边缘画派。
后岭南派,说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策略,是一种什么东西都好,关键在于它在今后如何更彻底地实验水墨。今后的发展倒是应该研究的事情了,因为“后岭南”它还会延续下去。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新水墨包括刘子建我们这班人该怎么走下去。刚才鲁虹提出消费文化,这一点,我想我们的一些创作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现在各种展览很多,每次看完,我心里都有很多想法。社会在发展啦,但我们的水墨画创作还是老样子 不过瘾!这次展览,是比较好的。关键就是作为“后岭南”的画家应该开始考虑怎样利用新的生存资源、材料,抓住历史的机遇,以使“后岭南派”更“后”。我想,“后岭南”必然存在于历史之中。
周 湧(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我把这个展览的作品分成三个类型:一个是按中国画的标准来创作的,就是以笔墨为标准,有很多好的作品;二是按现代水墨的标准来创作的;三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既搞一些创新的形式语言,也迁就一些笔墨效果。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把现代水墨跟中国画区分开来。现在很多展览把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造成批评上的混乱。我觉得,做现代水墨的就做现代水墨的东西,按照现代水墨的新的批评标准来进行创作。做传统中国画的,就按照中国画的标准来做。这两样东西都是可以一起来发展的。但是,饬窖饔斜匾挚£
还有就是,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是中国画,我认为我在做现代水墨。水墨画也好,中国画也好,都得跟今天的生活发生关系。刚才小敏也说了这个问题。
记得上次在深圳做那个“城市俚语”展览的时候,大家就谈到楼下展出的都是那些装置,包括录像;楼上展出的都是水墨。他们当时总体感觉到,楼上的东西都是关心哲学,很精英,好像是天上的东西。下面的东西就是现实生活中一出门就看到的东西。当时我的感受也很深,就是:我们的水墨作品怎样做到一拿出来就让人感觉到:“哦,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是我最深切的感受。
石 果(艺术家):
今天的主题是“后岭南”,不管它是画派还是文化现象,都值得探讨。在西安,很多画家搞“后长安”,可能是受到“后岭南”的影响。现在,中国画也好,水墨画也好,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新的发展。
有人把在西安发生的现象归纳为乡村表现主义,我觉得这个比把它叫做“后这个派”或“后那个派”感觉更清晰一点。但是,我觉得比较尴尬,第一我不打算加入后长安派,到那里边去搞一搞,我没有这样的想法。第二,我也不是乡村主义。就算是都市表现主义,也有南北之分。有北京、天津为一个板块的都市表现主义;再一个就是广东,我觉得这两块是比较有代表性。刚才,大家讲的表现当代生活跟表现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都是以这两个板块的特色为最明显的。但是,我觉得自己也不属于这两个板块,就是说我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都市。
我觉得我们有几个画家的身份比较可疑,到底他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当代呢?他是当代的人,但是,他不干当代的事,就有点奇怪,所以总是受到很多的质疑,这个现象也希望大家来分析一下。
今天,作为实验水墨这一块比较零散,分散在几个城市,都是一些比较个别的画家。好像脱离了原先的根子,现在又没有加入什么的东西,很个人化的一种现象。老是归不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情况,我想可能不能归结到地域来看。不管长安也罢,岭南也罢,作为过去的地方画派,现在这样延续下来,到了今天它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了。比如说像“后岭南”吧,也是各种各样的,包括黄一瀚他们搞卡通文化,跟原先那个岭南相比较,走得很远了,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化,
我在广东呆了17年,广东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广东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的美术馆,出头做这么多的事情,这一点在其它的省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几乎没有,包括北京。整个广东的文化构架,从官方的也好,学院的也好,民间的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自由主义的艺术家,大家能在一个很宽松的环境里边探讨这件事情,这一点在全国是非常罕见的。比如说我自己的水墨实验十几年,在别的地方恐怕就很不容易能够走出来。而在广东就有很多的机遇,这一点我跟皮道坚的想法是一致的。刚才几个批评家所讲的,提倡要介入生活,要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结合,这一点我不反对,我不主张非要搞一个文化。现在多元文化,每一个艺术家从他的角度去做他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自己,我觉得我目前这个尴尬的身份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让后人去说,让历史去说。我们还是要把它做得非常充分,不轻易去随波逐流。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一点也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
我很赞同这个看法!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当代的生活有自己独到的表现。如果失去这一点,我觉得,艺术家之称就是一个戏语。我建议罗一平博士谈谈他的看法,因为他主编过全国性的一些画册,对全国的状态有一定了解。
罗一平(美术批评家):
我刚来不久,还不到一年。但是,我对在座的各位艺术家的作品非常熟悉。比如黄一瀚老师,几年前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时候,我就不断收到你寄过来的这种卡通。但是我一直都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年龄,我一直都认为是非常很年轻的,大概是十几岁将近20岁的一批年轻人在搞的。而且里面的文化性很强。
我对广东的绘画有很强的印象,是从跟范迪安一起编《中国当代美术(1979~1999)》画册开始的。在这过程中,因为常务工作都是我在做,通过对作品和作者的追踪,我感觉到,一是广东艺术家入选这本书的有很多,二是广东艺术家的面貌特别多。当我把这些作品扫描挂到墙上供组委会审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就跟范迪安讲了一句:我感觉到广东现在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丝毫不亚于北京。
再谈画派的问题,我赞成皮老师的看法。一个画派它是一种精神,不是一种样式。我们现在讲岭南画派也好,南京画派也好,长安画派也好,其实无论是两高一陈,还是赵望云,还是傅抱石,在具体的创作中,他们并没有想到,他是岭南画派,他是长安画派,他是什么画派。其实他们所表现的就是他们所接触的生活,由这样特殊的生活情景中引发出大文化的思维。他们是对这种文化的反思,或者对文化的一种追寻。比如高剑父,当时在广东,革命气氛非常强,他生活在这里,自然而然要反叛传统那种以笔墨为中心的很文人的东西,自然而然会接受西方的东西。像刘子建你们来到广东以后,就要反映你们在这里的生存状态。其实,广东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有一个很开放的气氛,可以丢掉内地很多的所谓的语言的束缚。或者包括我们一讲到中国画,就将到线的问题、墨的问题、功力的问题等,我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画当中,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要去追求的问题。其实所谓的功力,它是一种表意的,是表达情感生命的一种形式。用墨也好,用线也好,只要把情感表现出来,而且具有冲击力,能够获共鸣,作品就是很成功的。
中国画家思想很沉重!赋予自己太多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能使他老在要锤炼一种风格,或是老是被一种方式所束缚。而不能像比如毕加索那样:毕加索没有赋予自己很重的使命感,能够不断否定自己。而中国的艺术家非常不敢否定自己,这除了因为传统之外,再就是他自己在难为自己。
我来到广东以后,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广东美术馆。我认为在中国的美术馆里,它是办得最好的。为什么呢?其实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地域的,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它同样是一个思想资源。这样一个美术馆它所着眼关注的、确定的,就是让人家能够通过这个美术馆看到你这样一个地区,或者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考。我就感觉到广东美术馆没有把自己划分得很区域性,它关注的东西,实际上是把自身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下。包括我们今天搞的这个展览,我认为是对20世纪的中国水墨文化应该何去何从的思考,也是对上个世纪水墨发展的思索。
说到画派的问题,我认为,后岭南是一个话题,后岭南是一个精神。有这么个话题,大家就能坐在一起;有这么一个精神,大家就能凝聚在一起。何况,岭南画派的这种精神,我们开始给它定位,它就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它就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它就是一种革命的精神。有这么好的几个概念来支撑着我们,我们何乐不为?在这么一个后岭南的话题下,经常聚集在一起,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做一些交流,经常思考一些问题。通过互相之间这样的火花的碰撞,我相信,我们的艺术,将能够领中国的水墨绘画之先。
其实,今天在座的艺术家,在中国水墨艺术中,已经是走在非常前列的。作为你们来讲,代表着广东的文化,代表着广东的水墨,实际上也是广东水墨在全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马文西(艺术家):
这次能够看到这么多作品,觉得大家都有热情为中国水墨文化争取自己的表现,这种热情很好。
这些年,因为觉得自己的探索有一定局限性,希望到外面去看看,所以我就去了日本留学。日本虽然是汉文化圈,它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但是到了近代,他们吸收西洋的东西比较多,在制作方面有它独到的地方,材料运用方面都比我们丰富。后来我又到美国去,体会就更深。
在创作上,我们一般都是参照西方的思维,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但是就我个人的学习经历来讲,我最痛苦的地方,不是在对西方的学习上,而是在国学功底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西方的观念要学习,更重要的,还是在国学方面更加承上启下。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新的时代以一种具有东方文化的精神,对现代文化做出贡献。
方 土(艺术家):
刚才大家谈到感受到广东文化氛围的宽松,我觉得这种宽松对于水墨的探索不一定是很好的环境。尽管艺术家不一定要有太负重的使命感,但是因为广东太宽松了,所以才导致了这次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的命题很准确)呈现了广东的新水墨的现象。
10年前跟10年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包括他绘画的艺术倾向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倾向的不一样,体现了广东跟外地艺术家的差异。广东的语言是越来越个体,并延续了它本来的一些东西。10年前我们跟一班人都会找出一些课题来争吵,好像这10年之后,包括到现在大家见面其实都没问题了,每个人的艺术观什么的都没问题了。有些人好像就被俘虏、被同化了。那我就觉得新水墨对中国的发展这种监护的责任,不是说负重太大,而是太轻了。我就说这么多!
苏小华(广州美术馆馆长):
刚才很多人都说是外来人,我是典型的土著。我从来都在广州这个圈子里头,学习和生活都在这里。这此展览有很多历史照片,我就从那个大阿龙说起,那个大阿龙的时候,我好像也是那个分子。当时,印了一张名片以后我就不知道干什么的。我们常常谈到什么“新”和“旧”,我觉得什么叫“新”、什么叫“旧”很难说。比如,以前广州美术学院就在晓港新村,我们家在1957年搬到那里住确实是叫新村,房子全是新的。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才从湖北搬过来的,就在我们家对面。那时候确实觉得广州美术学院像宫殿一样,很漂亮。但是那里现在还叫晓港新村,却已经破烂得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新”与“旧”是不是这么重要?好像“好”与“坏”比新旧更重要一些。追求“新”不一定就是那么高的境界。
再就是使命感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画家,他能承担那么重的任务吗?其实这个社会是一些经济力量在支撑和组织着,而我们是很次要的(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经常在很多场合都是可有可无的。
刚才还有先生讲了毕加索,我觉得这还好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有点生路。我想一个人的终极目标很重要,如果一定想进入美术史,挑着很重的担去走,也许到最后也进不了美术史。而我的终极目标只是我想生活得愉快一些,那么我每天都会很健康地生活。可能,这里边就有这个区别。
广东美术馆搞那么多活动,我觉得做得很好,作为同行,我衷心祝贺他们越做越好。
李劲堃(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
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恰当,我比较欣赏前面两个字。这个展览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认真。后岭南的出现,与其说是一个现象,倒不如说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变成现象已经是一个经过若干年的一种转变,从1993年到现在,这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这些现象能够糅合在一起,搞这么一个隆重的展览,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刚才很多理论家在探讨如何让西方去关注中国绘画,我想这可能是一厢情愿。就等于在20年前,我们的格局和实力还没有出现之前,谁会来这里开一个很隆重的会议?我想这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家在对当下各种作品的现象加以关注;二是当下各种艺术家的探索要努力一点,然后形成更好的局面。
郑 强(深圳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艺术家):
作为艺术家,从自己的创作状态,从心境方面,我很欣赏苏小华的心境。我觉得说到底,艺术家是很个体的事情。我不同意刘子建,好像说得非要形成一种什么关系。我觉得艺术创作是一种现象。艺术批评,批评家实际是在这些现象里边找到支持自己理论的根据。批评家不能涵盖整个美术创作现象,实际上,想涵盖也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找到跟自己研究的课题相关的那些创作现象加以研究。批评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不可能批评一切美术现象,他只能批评一部分的美术现象。所以,从这个现象讲,我想我们搞创作大可不必有太强的历史归宿感 硬要把自己加入一个派别才安心。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就比较放松,我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确确实实是自己想做的。如果我这张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就把它弄出来。将来怎么样,我没有什么把握,也可能将来一点影响都没有。我觉得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生存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左正尧(广东美术馆研究部策展人、艺术家):
刚才听了很多批评家和同行的话,我认为我们在这个谈话过程中,过分沉迷于自己的专业了,特别是我们画画的这班朋友。特别是刘子建先生,我觉得刘子建先生是很执着。这种执着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这种沉重的使命感会把我们弄得喘不过气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欣赏郑强这种心态。就说生活首先是应该轻松愉快的,我觉得快乐是第一的,健康是第一的。这是一个观念,就说我认为不要太沉重。
此外就是,我们是不是把眼界再放宽一点?我们要看到在我们生存的状态当中,更多要反映我们所处的时代状态。在这点上,王璜生馆长和罗一平老师的探讨,我非常赞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眼界放远一点,不应该仅仅去看这种技法的东西和笔墨纸张这种东西。
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美术馆和看国外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们真正感动的是作品本身,是他们如何把当下的这种观念和生活状态,利用今天所能用的材料来表现出来。只有这种作品,才让我们真正感动。你会觉得,你真正不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去用。我很有感触的一点是,比方电脑的运用。我们电脑的运用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但是我们在今天谁也不会去探讨电脑的问题。如果我们当中有谁不会去用电脑,就会被淘汰。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什么好去计较的了。我在平时更多地关注年轻一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比方说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我会更多地关注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能够提醒我们该注意的和我们该怎么走的问题。因为未来才是最主要的,我们必将会过去,我们如果一直沉迷在自己这点所谓的水墨、连自己都搞得糊里糊涂的材料里面去,我觉得太窄了。而且水墨本身,的确有它很多局限性。这个材料本身,比方说纸张,它能够永久的保存?它不发霉?它不容易破烂?然后颜色也非常鲜艳,非常的光彩,非常好用,如果真有这种材料的出现,我觉得水墨就不是问题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艺术家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不仅是造型,对材料的运用都非常优秀。但是很遗憾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材料,而这种材料的局限性,使我们再聪明的人在材料本身面前,也会有时候变得有点束手无策。而且也会使得一些优秀的东西张扬不出来。
在这一点上,我也一直在思考。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一定死抱着这种材料不放?或者去钻牛角尖一样钻进去?那么它就呼唤着我们对这种材料放宽来思考。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表达的方式,不要仅仅局限在这种表达当中。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卢小根(艺术家):
我的身份比石果还要尴尬,我是在浙美版画系毕业,然后做设计教育,现在自己玩水墨。三位一体地合到一块去了。我其实更尴尬!
但是,我觉得,你喜欢什么,你就做好了,至于贴上什么标签,都无所谓。比如说,说你是后岭南,你是新水墨,是人家说的事,不是你自己想要当后岭南、新水墨这个问题。刚刚罗一平老师讲的就是,要保持这种宽松的心态,像毕加索他不一定把自己放到什么立体主义或者什么其他主义的位置上去。他自己画就自己画,他玩得快乐。
这一点上,我的心态跟苏小华有同感。我现在做的事情,我现在所从事教学的工作,跟我玩的水墨距离比较大,我就想,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对这种媒材感兴趣,所以就玩下去了。你像这么些年来,后来回到浙美,在国画系毕业。所谓再修炼一下,传统的功夫又回来,再按照自己的想法玩下去,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面貌。我还想继续玩下去,也没有担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感,说要在这个水墨的改良、创新,或者干嘛,要做出一种成就,我没有这种负担,因为这不是我本身的职业。
按圈子里头一些艺术家的看法,我觉得太过。一些画家很急,他想着作品投放到市场以后的成功率比例,通过这来证明他自己在江湖的地位,我觉得这一点没必要,一点都没必要!
刚刚苏小华也讲到,我们当画家的,其实也是很边缘的人群。这个社会里头,这个文化工作已经是很边缘了,美术就更边缘了。既然大家已经走到这条路上来,按照自己喜好的去做,那么就努力去做。学学王璜生馆长,把广东美术馆经营得风火。感谢广东美术馆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大家玩一下,一起开心一把,这样就收到很好的效果。谢谢!
陈 泱(独立策展人):
我提两个例子,一是南美洲的例子。南美洲,显然他们的方法论,现在是作为最强力的文化批判和极其具有同情心的文化方法,被所谓的西方世界共享;二是日本的例子。事实上,日本有很多非常具有传统色彩的文化方式,也在我们称作“西方”的世界里面被广为流传。所以从方法上来讲,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来表达我们的水墨,不要让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办法进入这个水墨的世界。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水墨其实无所谓新旧,水墨是非常丰富的视觉经验,包括心灵体验,这是任何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共享的。所以,一方面,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直接传达,让非华人来共享。另一个方面,由于这个媒介越来越多,反而让我们最终发现这个媒介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比如在水墨当中所强调的这种最简单化表述、这种节奏、这种变化、这种理念、这种张力、这种气韵等,其实跟录像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是在讲时间性的变化,以及那种微妙的人在放慢步子和放慢思维速度之后慢慢体验着的东西,而且它所体现的价值也是很饱满的可波及力。
所以,我觉得水墨不仅是一个仅供保存的画种,完全不是这样。水墨实际上是有其有生命力的,而且在方法论上面,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样式。我觉得水墨的视觉经验和精神经验是 尤其在21世纪现在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发源的媒介,一种语言。因为过去10年、15年当中,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呈现,往往成为海外二战以后样式的一个呈现(当然我说的有点偏)。所以,我觉得,在谈到水墨问题的时候,特别关键的就是,如何呈现水墨和水墨所波及的饱满的视觉经验和精神风貌。谢谢大家!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
今天的研讨会开得非常热烈,谈了很多有趣的话题,而且有些还是交锋的话题。在广东可能这样的交锋,以及这样热烈的研讨会还是比较少的。非常感谢20多艺术家这么认真地参与了这次展览,很多人都专门创作了大型的作品,花了很多的精神,这是对我们广东美术馆的工作极大的支持。也感谢今天到会的批评家,希望大家今后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广州 影像三年展 2025 Guangzhou Image Triennial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