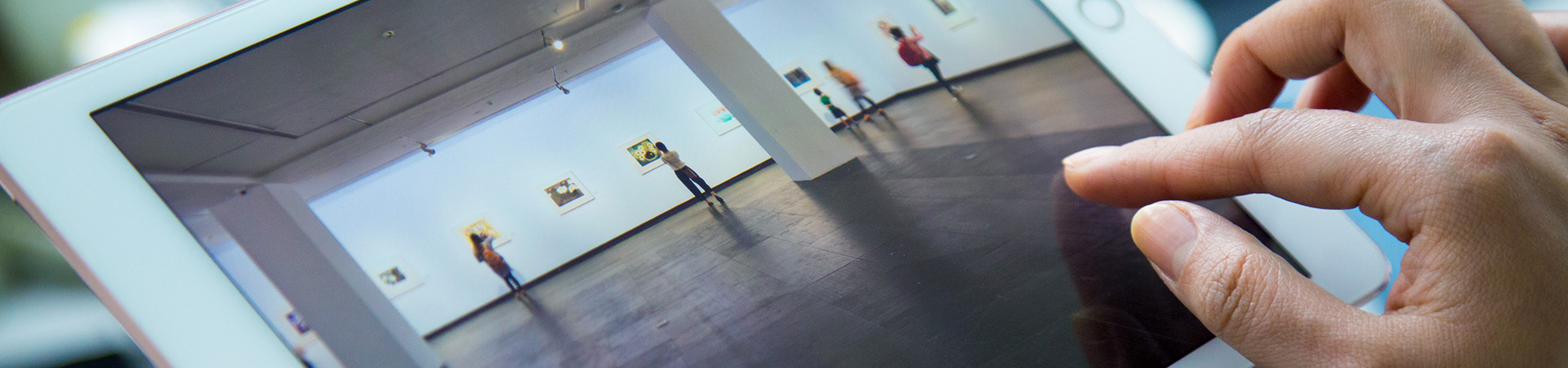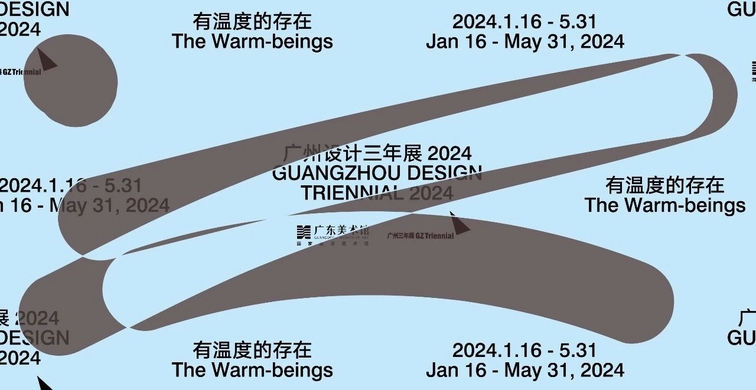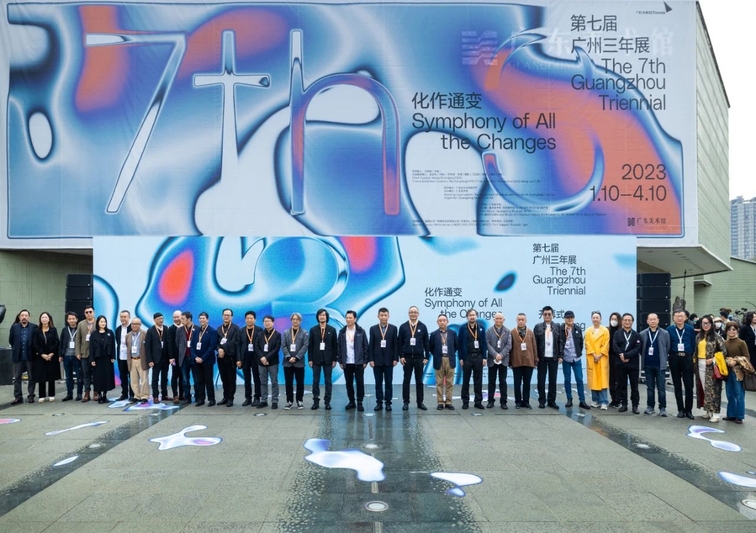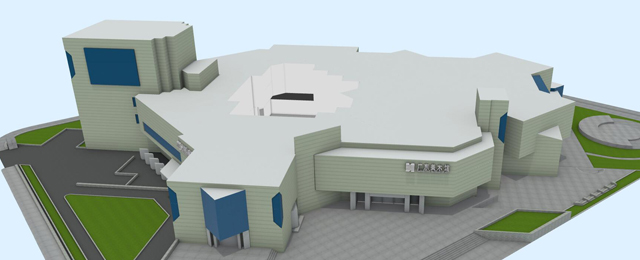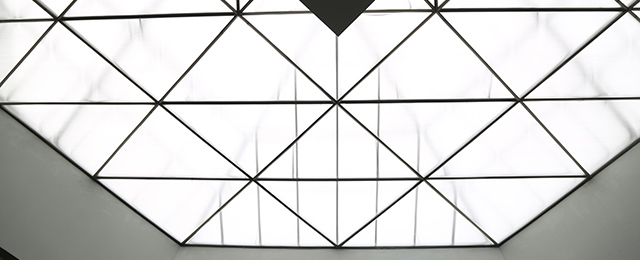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父”之为父--石鲁《转战陕北》一画的图像学分析(郑工)
录入时间: 2007-08-23
引言:“父”是一座山
父,不仅仅是“男人”的概念,而是“家”中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一家人的靠山。故,山,是“父”的象征。人们对“父”的崇敬,与其说是出于“爱”,毋宁说是出于寻求“保护”的潜意识,出于对“父权”的敬仰。在中国人的伦理观中,君臣关系即是父子关系。宋之山水画,那峰峦叠嶂,就已被比喻为君君臣臣--“君”是群峰之首,“君”在高山之巅。(郭熙1936)那么,在石鲁(1919-1982年)的《转战陕北》一画(见图1)中,在他塑造领袖形象时,是否也具有“父是一座山”的观念意识呢?
这里,引用一个回忆片断--那是1995年杨小彦对杨之光的访谈,其中涉及到石鲁:
杨:……我与石鲁很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59年全国美协组织了一批当时相当优秀的画家去北京搞创作,我当时就与石鲁同住一房。我的创作是《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石鲁便是他那张有名的《转战陕北》。
彦:《转战陕北》据说当时就有非议。
杨:私底下还是很让人服气的。我记得有一天王朝闻来看草图,他很欣赏石鲁的这张画,但他问了一个问题:主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石鲁的回答很有意思,我是个画家,我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争执起来,王坚持说必须考虑,不画上去而已。石鲁坚持说画画的只考虑画面上的东西。
彦:今天看来这个争论很令人深思。
杨:当时其实我们大家都想创新,都想在传统中弄点新东西出来。石鲁当时就跟我讨论过这些问题,他认为国画在情节与写实上无法跟苏联油画比,还是要发挥国画自己的特长。
(杨小彦1995)
为什么王朝闻坚持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石鲁拒绝考虑这个问题?当时作为理论家出场的王朝闻,面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其关注点必然是主题与情节。“主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是针对“转战陕北”这一历史主题所提出一种叙述的要求。叙述,或曰叙事,是主题性情节绘画所常用的手法。而石鲁的拒绝,是想脱离“叙事性”的表现,他要“发挥国画自己的特长”,从“象征性”的语言入手。因为象征,才可以超越具体的时空限制,不考虑具体的环境及其细节,甚至也不考虑情节的“合理性”。石鲁的《转战陕北》一画,有主题有情节,却没有遵循叙事性的原则,另辟蹊径,以象征性的手法描绘领袖形象,而且以其喻之为“山”。但真正的喻体并不在主席形象本身,而在于他身后那座穆然耸立的红色山峰。(见图2)主席的形象实体被“虚“化了(如采用“背影”形象),而中国画中的“虚写”正是牵引观者思绪的关键之处--这才是石鲁所要的“画面上的东西”。
如此,也就可以很合理地解释石鲁为什么要在主席面前置一悬崖。在画面上,这一垂直线延展了主席的形象,使“山”的形象与人的形象浑然一体,既有“巍然屹立”的喻意,又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含义,表现出战争的严酷性及所面临的历史转折点。所以,在作品完成后发表的“创作谈”中,石鲁很自然地言道:“风景(山水)画可以通过曲折的关系表现人的伟大,描写山的雄伟,就有人的存在,有时代感情。有时,它比直接描绘人物的画还有独到之处。”(叶坚等2003:57)
石鲁很注重画面的构成形式。他说:“余观虚谷画梅,作直交格形,何也?盖取其刚直、坚贞、方正之性为笔意也,摄其雪压冰封之态为笔理也,借其裂痕方格交叉之故为笔法也,达其气韵生动之美为笔趣也。故识笔墨当为画之主、客交织之生命线。”
(石鲁1985)在石鲁的眼中,抽象的形式可具有丰富的情意或特定的表达意味。譬如《转战陕北》之方构图,便意味着“至大至刚”,凝重、庄严、肃穆,均是“阳性”的以至是至上的“父性”之概念,以此表现“体积的巍峨”及力量的强度。这里,“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对毛泽东的崇敬与虔诚、很自然地将石鲁推入现代“圣像画”的创作状态中,而他的种种形式意味,也就有可能被引发到另一层面上加以阐释。
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而寻求意义的指向必须追寻思想。石鲁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不是单纯玩弄笔墨游戏的形式主义画家,但他又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谈,不偏废。其有一言:“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矣。”(叶坚等2003:160)这种思想,是一种个人的理解和追求。石鲁本质上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带有明显“乌托邦”的色彩。他可以逃婚,他可以只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可以因敬仰而易名--在艺术问题上,他尊崇石涛;在思想问题上,他尊崇鲁迅。回到思想的层面,我们是否可以从鲁迅的影响进一步解读石鲁呢?譬如,以“父”之名,看看鲁迅对“父权”的批判思想如何影响石鲁的创作,并兼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美术界创作毛泽东“背影”的现象。也许,这种解读会构成一种新的寓言故事,与历史主义的解释相去甚远。
将一个政党的领袖喻之为“父”,实际上也就将这个政治群体喻之为“家”,而对“父”的图像阐释也就落入到“家”的寓言中。其实,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群体中,“家”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革命大家庭”者,即是。
“家”的寓言之一:“恩”与“爱”
鲁迅关于“家”和“父”的言论,莫过于1919年1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们怎样做父亲”。文中,鲁迅着力批判的是封建传统的“父权”思想,尤其是所谓的“恩”。
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第一要义便是“孝”(“忠”由“孝”而阐发),而“孝”的思想基础便是“感恩”。因“父”生你,对你就具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做子女的要感恩尽孝--“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就应为长者所有”(鲁迅1919),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长者本位”思想。
所以,鲁迅说:“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那是天性所致,可称之为“爱”。若“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
(鲁迅1919)鲁迅强调“爱”,在于要建立新型的父子关系,去除父权思想,宣传为“父”的责任与义务。这责任是什么?那便是“解放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五十年代后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1919)一个牺牲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也具有时代英雄的色彩。可这些,能否在石鲁的《转战陕北》一画中加以读解呢?
画幅上,毛泽东站立在山势险峻的一边,面对着宽阔敞亮的山谷,“背”对观众。在展览会上,绘画作品的“背面”形象往往在观者的心理上产生“引领”的作用。不错,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解放者”,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概念,但石鲁并没有图解那些概念,他很巧妙地设置了一个特殊的语境,即“悬崖”。悬崖是一处险境,下有空谷,一般人都以为石鲁采用“隐”的手法,将千军万马以虚写的方式“藏”在山崖下,只在主席的身后以简洁的笔墨画出一匹马、马夫及一二个战士。“从哪里来”的问题交待了,可到哪里去?其实上,石鲁在画面上也回答了,即往高处去(见图3),毛泽东在此中途不过歇歇脚,偶一回身,放眼千山万壑,并且“东方欲晓”。路,从来都不是现成的,是人走出的。构图上,这里是一曲笔,有不少隐喻。譬如,画面的“前景”就是一片悬崖,而革命道路的前途则向上奔向远方。或者说,以“路”而言,是自下而上的,由近及远的,并与渐行远去的山脊叠合在一起。毛泽东立在悬崖,固然有纪念碑式的造型处理需要,而且位处画幅下方,与身后的山崖一字排开,共同担当着整幅画的重量,既是主峰,又是基石。在此险绝之处,毛泽东一人独挡,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现在想想,六十年代那些恶意攻击石鲁的人,说石鲁的《转战陕北》将毛泽东“置于进退维谷的绝境”,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幅画所被解读出的悲剧性内容。
不可否认,石鲁在创作《转战陕北》一画时,也具有“歌颂圣明”的思想倾向。但他的艺术个性及对鲁迅的理解,使他拥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毛泽东并塑造毛泽东的形象,并在“恩”与“爱”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兼顾的策略。譬如,在“恩”的方面,石鲁塑造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引路人的形象;在“爱”的方面,石鲁处理了给后来者让路的这么一个情景,即鲁迅所宣扬的那种父之爱,将今后的发展空间交给自己的孩子,让子女超越自己,也超越过去,比自己更强也更幸福。
尽管毛泽东本人也很推崇鲁迅,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棋手。但在五六十年代真正读解鲁迅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如何为“父”的问题上,作为领袖的“长者本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形象的主题性创作上,“父”者一定在上,而“幼者本位”只是在需要时才被提出。如石鲁的《转战陕北》一画,在毛泽东的形象之上只能置空,我们可以读解其为将来者预留的,但绝不可以出现犯“上”的迹象。在这一点上,石鲁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鲁迅所反对的“长者本位”思想也不可能在石鲁的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石鲁在延安的革命大家庭中生活工作了十年,经历“讲话”及延安的思想整风运动,而他对鲁迅的认识也在那时期形成。我们手中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去了解鲁迅对石鲁影响的程度有多深,但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不是鲁迅所能比拟。所以,在表现毛泽东的形象时,就难免神圣化。以“父”之名解读石鲁的《转战陕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父”,而是具有“灵光圈”的“父”--这“灵光圈”就出现在毛泽东形象的背后,以山岚之气染之。在基督神学中,光明也代表着神的意念--经由光明,世界被拯救,被教育,被改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是世界之光”。在石鲁的《转战陕北》,唯一的“光”,就被用在主席及他所率领的队伍上所出现的山颠上。
“家”的寓言之二:“单身迁居”
……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鲁迅1919)
我们不一定就认为,石鲁在表现“转战”这一主题时,联想到了石鲁关于先祖“单身迁居”的说法。但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我们又不可回避关于“迁居”问题,用正式的说法,即战略性转移。如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转移到了陕北延安;又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又再次率领红色中央政权离开延安,转战陕北。
为什么要以鲁迅的“单身迁居”之说解读石鲁的《转战陕北》呢?因为作为新兴的革命政党,在早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实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鲁迅是一位进化论者,他相信新的总要取代旧的,新兴的总是有希望的(后来他的这种思想有了改变,特别是他看到一些“革命”的青年所作所为之后)。这种唯“新”论,在鲁迅的言谈中随处可见,如他之所以扶持新兴木刻,就因为“唯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面”(魯迅《二心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
小引》),他相信,这种“幼小”的新芽终要长成参天的大树。看看石鲁的《转战陕北》,总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前景的山崖上处理成一个含苞待放的“幼芽”形状呢?(见图4)可能这就是石鲁隐含在画中的寓意,因为它切合鲁迅“幼者本位”的思想。延安,以至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成长壮大的地方,是早期的“革命大家庭”迁徙之所。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到达陕北并在此建立根据地,则是在“遵义会议”确认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作为延安革命圣地的开创者,毛泽东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紅軍),在陕北立住了脚,成就了一番家业。对于毛泽东而言,瑞金时期的红色政权并不是他的业绩,而延安时期的红色政权是他“成家立业”的开端--那才是他的“家”。这一段历史,很恰当地为“单身迁居”下了个注脚,而那后半句只是鲁迅沿用“进化论”的话语逻辑推理所致,与石鲁此画无关。
石鲁《转战陕北》一画的意义何在?他在讲述毛泽东这个“家”的寓言故事。譬如,“单身创业”者,且是“始祖”。在鲁迅的思想意识中,那才是“创造者”,是社会的“精英”。作为“五四“人物,鲁迅极力推重“启蒙”的工作。从《阿Q正传》、《孔乙己》、《药》到《祥林嫂》,鲁迅笔下的大众都是愚昧的浑浑噩噩的“庸众”,都需要被唤醒,而唤醒者应是先觉者,是社会的精英人物,是具有开创意识的人。在启蒙时代,先觉者必须占有一个高度,能够看到将来,这也就注定了他那孤独的处境。正因为“卓尔不群”,才能够“高瞻远瞩”,才能够“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一个家族的兴衰,原因有很多,而鲁迅认为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大家族鼎盛之际或正在走下坡路时,要能够“解放后来的人”,让子女“分立”,“结清旧账”,“开辟新路”。这不是“叛逆”和“不孝”,而是“天道”。“五四”之后的中国,从封建大家庭中“出走”的人还真不少。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出走,就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圈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周恩来是“出走”者,朱德是“出走”者,毛泽东也是“出走”者;而石鲁自身,也是原先那个“家”的出走者。巴金有一著名小说《家》,披露的就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境况。那时的“革命者”或曰“觉醒者”,有一个颇有时髦的话语,即“背叛家庭”。“背叛”的目的是脱离旧的,开创新的家业。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开创者,这是五十年代沿用至今的说法。在那时,石鲁不可能说新中国是毛泽东和他那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开创的,主席是第一位的,也是唯一的。故在画面上,毛泽东的周围不可能出现第二个人,而“单身迁居”的说法也吻合画面的实际效果,或许正是石鲁的创作意图。
回到石鲁的《转战陕北》一画,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三个层次十分清晰--第一层,近景,“幼芽”形的巨石,毛泽东在山崖上独立(颇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气势);第二层,中景,蜿蜒远去的山脊,毛泽东所率领的队伍正从山崖下攀登而上,准备继续前行;第三层,远景,千山万壑,仿佛“山呼万岁”!而这三层画面相对的含义则是:第一,引领子弟兵的“父亲”;第二,追随“父亲”的子弟兵;第三,亟待唤醒的工农大众,也是歌唱“东方红”的人民群众。
余论:“父”背的沉重与宽厚
“父是一座山”的观念本身就有一种沉重的意味。因为为“父”者必须担当,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肩。“父”的坚强与力量,在身体语言上很容易在背部表现出来,如“脊梁”。鲁迅就形容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中国人的脊梁”,这一语,在石鲁《转战陕北》一画中表达的也很充分。如毛泽东站立的形象,就通过背侧的方式拉出一条挺拔的直线,甚至因为过分挺拔而显出一个弧度--这就是挺立的“中国人的脊梁”!而他脚下站立的也是“山脊”,横卧在中国的大地上。
石鲁对毛泽东形象的图像解读,更多地从“父”之为父的社会角色方面去表现,而父的“背影”形象所具有的亲情与宽厚的另一层含义,即鲁迅所言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一面,在石鲁的《转战陕北》中并非主要。就“爱”而言,石鲁的表达略显得有些隐晦,或者说,作为毛泽东“背影”形象的首创者,其面对的政治压力也很大,前述的与王朝闻的争执就是一例,而作为本人,石鲁的创作意识也并不那么单一,这些都表现在创作草图的前后几次修改上。但在1962-63年,钟涵创作油画《延河边上》(见图5)时,他就完全离开了“恩”的主题,而对革命领袖内在的“爱”给予充分的关注。钟涵表现毛泽东的形象,同样也避开了正面的表达方式,选取了“背影”形象。他画的毛泽东背影不是“侧背”,而是“全背”,同时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很亲切很和谐地处理在一起,因此,那“山”的寓意(前者为毛泽东和陕北农民,后者为延安宝塔山)、那对“脊梁”的真切感受,那“父”
背的宽厚与慈爱,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一点上,钟涵比石鲁表现更得彻底--他更注重表现领袖身上的那活生生的人性,同时也表达
“为人父”者的那宽广而深厚的爱。
在毛泽东的形象表达中使用“背面”语言,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让人考虑再三的问题。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有关父亲的“背影”,最深情的表达莫过于朱自清的那篇散文(“父”之背影的形象也是出现在“送子出行”的车站上);而当代绘画中的有关毛泽东的“背影”,最深情的表达莫过于钟涵的《延河边上》。钟涵的这幅画稿,最初是由他那油画研究班的导师罗工柳所确定的。罗工柳也是从延安“鲁艺”走出来,五十年代留学前苏联,刚刚回国。那时,罗工柳负责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历史画创作,对于怎样画革命历史画,他的心中应该有个谱。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罗工柳创作的《前仆后继》有一个很生动的形象,就是背影,而作为牺牲者的“烈士”亦被蒙上了白布,也不出现正面形象。但他画《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时,还是使用了正面形象,可他却一再支持钟涵画毛泽东的“背影”。
随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后,进入六十年代,歌颂革命领袖,表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在中国美术界渐成风潮,至1964年的全军美展,可以说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圣像画”运动的前奏。“如何表现革命领袖”,就成为很严肃的政治问题。领袖被推上“圣坛”,必然要强化神性并清除人性,更强调神之“恩”而不是父之“爱”,在图像的表达上,也只能允许“正面”而不能使用“反面”(即“背影”形象)。这样,石鲁在1964年因为《转战陕北》而遭遇批判,而钟涵的《延河边上》一画在“文革”期间被毁,也就成为无法躲避的历史现象。
解读石鲁的作品,是进入石鲁的内心世界及其创作意识层面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许其本人并未表述过,或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当下的思想状况,因为处在创作中的画家,其思维不可能是单向度的,总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参合在一起,而本人也不会那么清晰那么理性。真正引导其创作的意识,常常都是朦胧的,像眼前的一束光,让艺术家不自觉地前行。不过,旁人的任何读解都只是一种诠释,是批注而不是本文。也许会启发更多的研究可能,也许会误导,甚或匡谬(还不包括带有恶意的政治性的陷害,如“悬崖勒马”之说)。其实,就是艺术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解释也只是一种注脚,而不是本文。本文只能是作品。
一般论及石鲁的绘画创作,多谈其“野、怪、乱、黑”的笔墨特征及形式问题,而较少在图像学的层面上谈论其意义世界。图像的特点在于表意,能够让人们注意美术作品内诗性的隐喻思维。尽管本文对石鲁《转战陕北》一画的重读,或多或少也包含有重建某种失传方案的企图,同时,在解释的过程中也有“重新创造”的因素。如果缺乏“重新创造”的解释企图,又如何将隐藏在作品题材和形式中那“只能悄悄透露而不能公开炫耀的东西”(帕诺夫斯基1987:35)显露出来?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重建历史”或“重现方案”,而在于如何“重现”。本文的意图也就在历史和社会文化更广泛的背景上,在一些话语所连接的关系网络中,去解读石鲁的《转战陕北》,力图传达出画家因种种限制无法或根本不能表达的创作意图,或许,这只是本文作者关于种种可能性的设想。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即鲁迅的话语是否就是石鲁创作的“原典”?
在结束本文时,让我联想到“文革”后罗中立创作的油画《父亲》--正面的大头像,应用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圣像画”的那种大规格的尺寸。罗中立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置换图像的手法,会引起中国人广泛的震惊与感叹。看来,钩沉一个“父”字,会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引发太多太多的内容。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英]贡布里希
1990. 象征的图像[M].
杨思梁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郭熙
1936. 林泉高致[M] //
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上海:上海神州國光社,4(40).
羅工柳
1999. 罗工柳艺术对话录[M]. 劉骁純整理,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鲁迅(发表时署“唐侯”)
1919. 我们怎样做父亲[J]. 新青年,1919,6(6).
[美]帕诺夫斯基,E.
1987. 视觉艺术的含义[M]. 傅志强译,辽宁:辽宁美术出版社.
石魯
1985. 石魯學畫錄[M].令狐彪整理校勘, 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杨小彦
1995. 与杨之光老师的谈话[J]. 画廊,(4).
叶剑、石丹编
2003. 石鲁艺术文集[G].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钟涵
1963. 谈《在延河边上》[J]. 美术,(9).
注释:
1.
即Iconology。又译为图像解释学。
2.
石鲁,原名冯亚珩,又名冯悭兰,四川省仁寿县人。1940年奔赴延安,因崇拜石涛与鲁迅,故易名石鲁。
3.
这里不是meaning(原义),而是significance,即由解释者所阐发的意义。
4.
1936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时,病重中的鲁迅曾发出一封电报,其中稱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是中国的脊梁”。虽然电文是冯雪峰拟鲁迅的语气及笔法撰写的,但写完后经鲁迅过目并认可,亦被视为鲁迅原文。
5.
钟涵说:“开始的创作母题是累赘的、不鲜明的,在过去接触到的题材中,我预选了许多情节,有毛主席、徐老同小八路在河边偶遇的情景,有散步,洗衣、饮马、汲水等富有生活气息的种种,我都想一一摄入画中。由于情节复杂、人物繁多,我脑中的基本画面长时期地纷乱而模糊,去年在延安画成了六种小稿,一齐寄给我们研究班的老师,老师帮助我肯定了一种,即近景上一群人在河边回过头来远望毛主席和农民缓步走过去的背景。这个小稿仍然不太好。后来,我尝试着从画稿上把中一片阳光前面的两个背景。我把两个背景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带点塑像和像征性的概括形像,这两个人物在素描稿上画了许多次,其中感到的主要困难是不会把亲切与开朗这两种精神状态统一地、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钟涵1963)
6.
据罗工柳言,因为董希文对此有所异议,钟涵一度将毛泽东的形象改画为正面,是罗工柳坚决主张改回“背影”。(刘骁纯1999)
7.
英国美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图像学家正是靠着对这些原典的熟悉和对绘画的熟悉,从两边着手,架起一座桥梁,沟通图像和题材之间的鸿沟。这样,解释就是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而且,这条证据不仅要能帮助图像学家确定图像所再现的故事,他还希望根据那一特定的上下文来弄清这则故事的意义。”(贡布里希1990:6)但鲁迅关于“父亲”的那些言论并不是在石鲁《转战陕北》一画的创作依据,
8.
帕诺夫斯基《图像志与图像学》一文中说:“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阶级、一种宗教信仰或哲学信念的基本态度--所有这些都不自觉地受到一个个性的限制,并且凝结在一件作品中。显然,这种无意识的显现将由于观念和形式二者中任何一种因素的比例受到有意识的强调或压抑而变得模糊不清。”(帕诺夫斯基1987:36)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冬日的寒凉抵不过大家的热情。 广东美术馆的这个冬天, 因为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