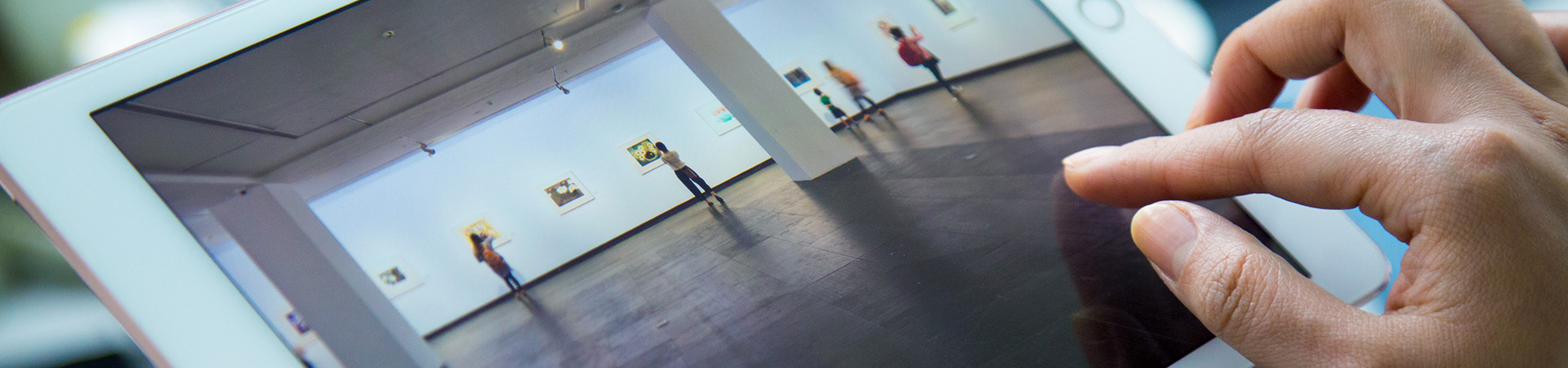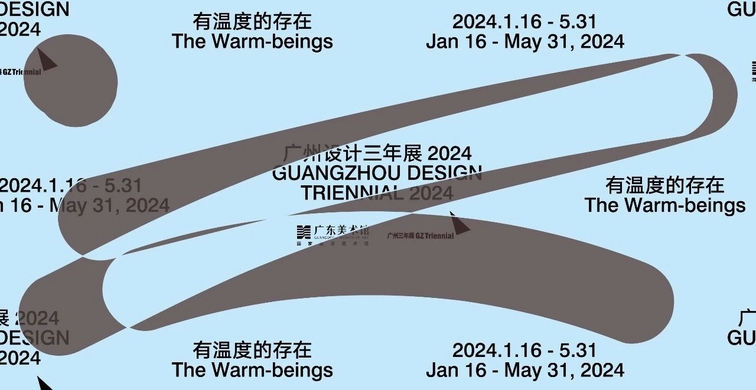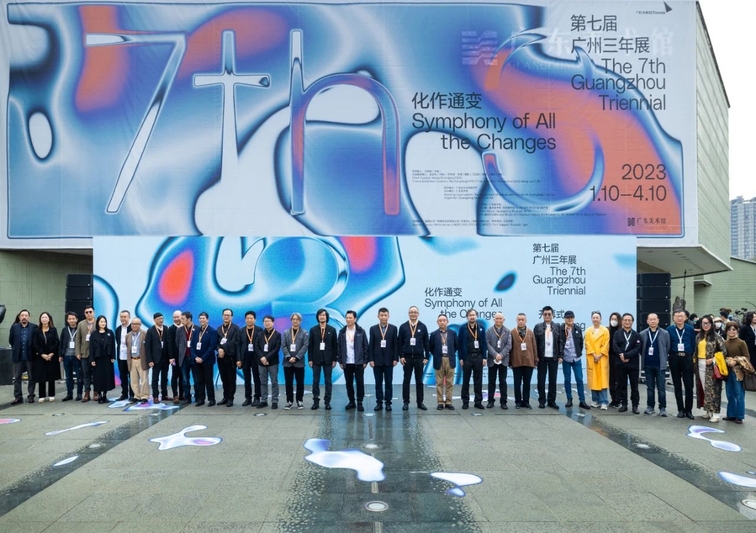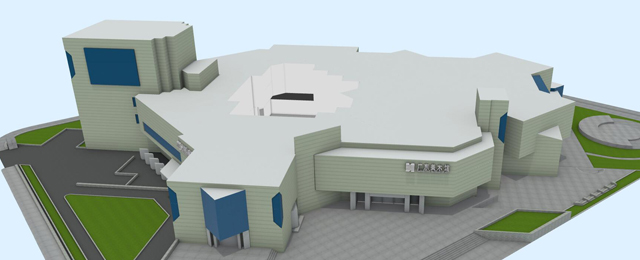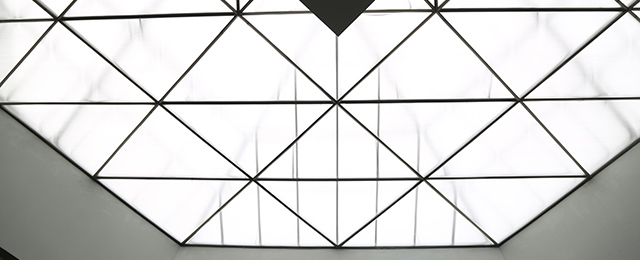追访石鲁早年行迹(水天中)
录入时间: 2007-08-21
我见石鲁是上世纪50年代前期,在西安北大街西北美协院内、长安兴国寺艺术学院的教室里。那时石鲁风华正茂,流露出踌躇满志的意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1974年年初,人们传说石鲁到了兰州。果然,石鲁出现在兰州友谊宾馆的餐厅里。他是来看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的。20年间,石鲁竟已老态龙钟。实际上,当时他不过五十多岁。那20年大概是大部分中国人衰老最快的20年,或者说是成熟最快的20年。究竟是“成熟”还是“衰老”,就看你在那20年里处于什么位置了。
1993年秋天,我从成都南门外长途汽车站搭车前往仁寿寻访石鲁故里。[1]仁寿在成都市正南,汽车从彭山、眉山往仁寿,进入山区,看到山间水库和正在采收的金黄桔林,便到了仁寿。仁寿古称陵州,北宋诗人、画家文同(字与可)曾在此地当地方官,写过一些很有趣味的小诗。如《可笑口号》,其一为:
可笑山州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无书籍兼图画,便不教人白发生。
李特寿有诗吟仁寿:
真成蜀道路蚕丛,万壑千岩一径通,忽见人烟三百户,古陵阳在乱山中。
诗人真实描写了仁寿的山川形势,汽车从山道绕出,远远地看到了奎星阁。那曾是仁寿的标志,当年石鲁从乡下进县城,也该是看到奎星阁便知道进入县城了。
石鲁故家在仁寿县城正北的文宫镇(一作文公镇)松林乡。解放后,这一大片宅院由当地学校、粮仓、公社等等好多单位占用。我去时还有一些旧日的房屋,大门、二门保持着原样。在一列石阶之上的院门正中,镌刻着“抱一庐”横额,两侧楹联也是砖刻而成:“名高食座三千客,友伴山林十八公。”
据石鲁本人回忆,他的高祖父冯家驹从江西景德镇来到四川,初入川时以贩运药材、棉花为生,后来获高额利润,便在文宫镇置田安家,成为当地大户。到他曾祖父时,已有田产5000~6000亩,佃户近千家。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在清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同志会会长(一说为保路局局长),以他家族的团练为武装后盾,向端方率领的清军叫板。仁寿乡民素以刁悍好斗驰名蜀中,冯家团练又有从外地买来的洋枪洋炮,真要打起来,宁静的松林乡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好在保路风潮以清朝覆亡而结束,而仁寿冯家的影响,在清末民初达到了颠峰状态。
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日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石鲁的三叔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他在外经营工商实业,又从南方买来大批卷轴书画和善本古籍,冯家宅院经他设计改建,也显得气象一新,更添了一些文化气息。
我从破旧的石阶走进冯家宅邸,除了充作乡政府仓库的旧房外,只有一些断墙残垣。有一些新式房屋,是这里建起小学后新筑的了。50年代初,石鲁的叔父辈有好几个在“镇反”、“土改”中被处决,青年人早已散居各处。我们从“秤杆山”上向两边眺望,山林在初冬的雾霭中别有一种苍润静谧的韵致。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然后进入成都东方艺专。他从东方艺专回到家乡,曾当过小学校的教师,并带领学生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当年的那些孩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个年轻的冯老师?现在,整个松林村如此寂静,一代又一代人的聚散生息,悲欢离合,似都已融入越来越浓的白雾。雾气从土地中升起,秤杆山下的农舍和竹木都已化为水墨淡影。我曾想通过仁寿之行,使石鲁早年生活的印象变得清晰起来,而现在,反倒更加难以捉摸了。
石鲁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在这里出生的。也许我所站立的草地,就是他出生和学步的庭院?那是1919年12月15日[2]。石鲁自述,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保康泰。到开始读书时,他却变得顽健好动,当他顽皮嬉闹得过分时,哥哥姐姐便叫他“糠猴子”!“糠谷子”!糠是永康之“康”的谐音,在农村,“糠”是下脚货,斥其不成材也;猴子是机灵好动的,斥其无法管束也。石鲁的机灵好动,在他成年以后仍然如此。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直到他12岁前后,这个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国、英、算之外,还有石鲁所喜欢的图画课。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他自学画画成效显著,以致他的二哥冯建吴假期回仁寿省亲,看到小弟永康所作六尺整纸的水墨中堂时大为惊异,决心请母亲准许小弟随他去学画。
东方艺专[3]是冯建吴和他的几个朋友办起来的,教师多是在上海学过美术的青年人。段虚谷任校长,冯建吴任国画系主任兼教务长,后来还担任过校长。他对小弟永康的情谊,是兄弟骨肉亲情、师生感情和艺术伙伴友情的综合。石鲁艺术历程的初始阶段,是在冯建吴的扶持和指引下往前走的。除了二哥冯建吴,石鲁的一个姑姑冯璧如,是学校负责管理女生起居生活的女舍监。由于这些关系,石鲁不但免试入学,免缴学费,而且被老师们称作“冯老弟”。这个称呼也为同学们欣然认同。这固然是四川人特有的幽默,但也可以看出这位最年轻的学生的特殊身分[4]
据石鲁自述,进入东方美专的第一年他继续专心学习国画,除了埋头作画,别的活动很少参加。每天晚上,则听他哥哥给他讲绘画历史故事,那些安贫乐道、气节高迈的画家成为他生活的榜样。尤以石涛和八大山人,最为他仰慕。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在埋头作画之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和各种课外书刊。促成这一变化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冯建吴反复喻示,想成为一个画家,必要有高超的文化修养;想画好一幅画,必须具备深厚的“书卷气”。另一个原因是在一次与同学争吵时,别人说他是“连小学常识也没有的人”!这使石鲁大为震动,自此发愤读书。
从石鲁以后的艺术发展看,从仁寿老家到成都东方艺专随冯建吴学画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的艺术发展以至价值观念的构成,都有极深的影响。虽然他在后来的某些时候,力图清洗这种影响,但事实证明那是无法清洗的。他与哥哥冯建吴的关系也是如此。[5]
冯建吴后来任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在他去世后举办的个展中,人们隐约感到兄弟二人在艺术趣味上确有内在的联系。
石鲁在东方美专的第二年,冯建吴要去上海拜师访友。冯建吴与王震有一段师生之谊,石鲁对王震的作品也极为欣赏,他托冯建吴带去他的中国画作品,请求王震指点。此后,冯建吴对石鲁的关怀照顾却不似原先那般周到,因为冯建吴与一位女学生热恋。这使石鲁感到被哥哥冷落,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正是这种失落,使石鲁走出了冯建吴的庇荫,离开了冯建吴的光环。他开始和同学们有了真正的交往,他发现这些青年人所想和所谈的艺术,与他们兄弟二人素日所想所谈的大不相同。同学们认为传统水墨画是没有出路的,大家感兴趣的是与现代社会更为合拍的西画和工艺美术。在年轻人中间,不懂西方绘画、不学西方绘画,似乎就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石鲁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或者按有些熟悉他的人的说法,他是个“好表现”的人(“好表现”实际上是艺术家标新立异的创造欲的别名)。他开始研习西画,并且很快就初见成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峨眉山旅行写生活动中,石鲁用水彩画和水墨画互用的方式,作了三十多幅风景。现在有许多人把石鲁想象为一个豪爽粗犷的艺术家,实际上石鲁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表现出特殊的机灵、巧妙和智慧,这些素质体现在他的各种工作和活动中。石鲁的水彩加水墨大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被老师、同学争相索要,一抢而空。就是从那时开始,石鲁开始疏远了传统诗文书画,转向与时代气氛较为接近的艺术。他到达陕北后,曾反省当初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追求,认为那是“把自己的眼睛挡起来,不敢看新东西,把耳朵捂着不敢听新声音,把嘴堵着不敢尝新味道”,是一种“高雅的愚昧”。但在经过世事沧桑之后,他重新从新的愚昧走向“高雅”。那已经是他暮年的事了。
石鲁之离开东方美专,是由于美专改制为东方职业美术学校,要求学生具有正规小学和初中学历。石鲁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母亲又对他学画不满,实行“经济封锁”。在内外夹攻之下,他返回文宫镇,于1937年年初到文宫镇中心小学当教师,为初小、高小几个年级教国语、历史、公民、劳作课和全校各年级的图画课。石鲁自己回忆说:“如果在东方美专时我曾喜欢埋头在画中的话,现在就喜欢狂热的教学工作。”一个学期之后,石鲁的教学工作受到老师、学生的一致赞扬。特别是老师们觉得他善于管理女生,很受女学生的欢迎,所以学校让他担任高小女生班的级任老师,即相当于现时的班主任。
此时适逢抗日战争开始,全体师生投入抗战宣传活动,学校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他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演讲、唱歌、演戏、写标语、画漫画、办壁报……这些全是石鲁喜欢做,也做得非常出色的事。这一段宣传活动,是石鲁最为兴奋的日子。因此,当学校终于恢复原有的按部就班的教学秩序时,石鲁大为不满,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促使他离开故乡,因为在故乡没有他所向往的生活境界。这是在他处于青春期的骚动不安时发生的事。
就在石鲁对学校里冷清和刻板的生活方式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父亲病故了。石鲁以父丧为借口,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回家另谋出路。在做出种种设想和安排之后,他与家庭达成又一次协议。母亲同意给他学费,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上学,条件是他同意与母亲为他找的姑娘成婚。
石鲁是在办好了在华西大学上学的手续之后,才返回文宫镇结婚的,新娘叫张艾如。婚礼之后第三天,他便离家去成都上学。石鲁的母亲这才知道她的儿子同意结婚,完全是为了取得外出求学的权利,这使她十分伤心。
1938年秋季学期开始时,石鲁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对于石鲁来说,华西大学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
成都城南的这一片地方,叫“华西坝”。抗日战争期间,南京金陵女大和山东齐鲁大学两所教会学校也迁移到这里,三所教会大学的师生聚集于华西大学校园,华西坝成为成都最富文化气氛的地方。来自东南沿海的大学生、大学教授和许多外籍教授改变了华西坝原有的文化气氛。不但校园内文采郁郁,连大学周围的茶馆酒店,也成了四方学子的天下。
石鲁回忆华西大学的生活,有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概。名目繁多的课程首先给了石鲁下马威,历史社会学系一年级开设历史、社会学原理、人类学、逻辑、国文、英文等课。逻辑和英文他完全听不懂,他没有学过英语,而由外国教授用英文讲授的逻辑他当然更无从学起。最使他窘迫的是,他是拿了三哥冯伯琴在北平上大学的证件报名入学的,所以还不敢让老师和同学觉察他不懂英语。他干脆以在北平已读完大一英文为理由,申请免修英语课,另外选修文学系的古典诗词,教育系的伦理学等课程。在课外,他和几位谈得来的同学组成“励近学会”,学习和探讨与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学术问题,并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华西大学的生活,像在他眼前打开了新的门户,使他感觉到世界的广阔和文化的繁杂,开始懂得生活的道路有各种不同的走法。
我在华西大学校园里漫步时,曾向一位教师模样的中年人打听,解放前的“历史社会学系”在哪一座楼房,他摇摇头,说没有听过这么个系。我们在一片树林边看池塘对面的钟楼,池塘里满是枯黄的荷叶和枝梗,红砖砌筑的钟楼在夕阳下重新辉煌起来,它肯定包藏了很多故事。
与文宫镇和东方艺专相比,华西坝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校园的开阔和图书馆、教室的宁静都远胜文宫镇小学和东方艺专。但石鲁此时缺少埋头读书的心境,自从抗日战火燃起,石鲁带领学生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之后,与现实生活无甚联系的学业,已经从石鲁心中推远,他在犹豫和企盼中度过了华西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寒假前,华西大学校方宣布,由于战时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明年开始,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作为大一学生必修课,学期结束时必须通过考试。这对没有上过正规中小学的石鲁来说,可真是难以逾越的关卡,他曾想利用假期补习英文。但仔细一想,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头补修中学六年的英文课,根本没有希望通过期末的考试。看来再以原来的学历资格继续上大学是此路不通了,他只能返回仁寿老家。但一想到文宫镇松林村的沉闷和停滞的日子,想到母亲为他娶来的妻子,回仁寿的这条路更是不能设想的。
在左右为难的关头,石鲁想起了他的堂妹和表妹曾给他讲过的陕北抗日军政大学,那是一个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不讲学历、不收学费,不学英文数理化……他觉得这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
有许多记述石鲁生平的文章、资料中(包括我自己的文章)都把这一转折性事件的起因说成是石鲁听了林伯渠的讲话。林伯渠向成都青年学生介绍抗大确有其事,但听到林伯渠讲话的不是石鲁,而是石鲁的堂妹冯月窗、表妹张素娟。她们俩在成都协进中学上学,在学校里听到林伯渠介绍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谈到延安抗大欢迎抗日爱国的青年去学习,并曾介绍她们去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石鲁找到冯月窗和张素娟,再次询问了去陕北读书的事,得到堂妹和表妹的证实之后,他下定决心去陕北,并请两个姑娘替他暂时保密--不要告诉家里,因为他估计他母亲和已经成婚的妻子是会阻拦的。石鲁带上母亲给他用作交学费的100块钱,躲过在华西大学宿舍同住的哥哥,离开成都向西安出发了。
从成都出发时,他搭乘开往绵阳的长途客车。在绵阳,石鲁以
50块钱买到一辆自行车,把行李架到车后,沿川陕公路北上。
抗日战争时期的川陕公路,是大后方交通要道。成都到西安,成都到兰州,一直通行定期班车。虽然人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破旧汽车上耽延许多时日,但还不至于非骑自行车或者徒步往返不可。石鲁为什么放弃乘车而买自行前往,颇值得玩味。我猜测,也许是为了体验一种新鲜的旅行经历。
从绵阳往北,临近四川盆地北缘,他骑车过梓潼、剑阁、剑门,过嘉陵江到广元。广元再往北,公路进入秦岭山脉,他常常得推车上坡,这样一直到陕西省境的宁羌。这一路他结识了一位叫乔之栋的旅伴,他本来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是靠石鲁的接济才到达目的地的。在宁羌(现在叫宁强),石鲁卖掉那辆自行车,买汽车票乘车到宝鸡,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吃苦流汗自不用说,还得通过道道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身分来历。幸好他有华西大学学生证件,得以平安抵达西安。在西安北大街的“中国旅社”住宿一夜,第二天就去八路军办事处。
石鲁自述,他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后,办事处负责人宣侠父接待了他。他让石鲁住进办事处招待所,然后向他介绍了去陕北求学的情况。抗大和陕北公学目前都不招生,所以暂时不能去延安。石鲁此时已无退路,他向宣侠父表白了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办事处介绍他去安吴堡青训班学习。[6]
安吴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石鲁原先的目的是到延安上抗大,对这个位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训练班”则觉得兴趣不大,但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即离开西安经三原去安吴堡。他从成都带来的100块钱到西安时已所剩无几,到三原后则身无分文了。他是靠卖衣服得到20块钱,才到达泾阳县蒋路乡的安吴堡村,找到“中国青年训练班“的,时为1939年1月。陕西泾阳在当时不属八路军控制的区域,但安吴青训班却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石鲁到安吴青训班,实际上已经“投身革命”。[7]
石鲁早年的经历,虽然不能与他在延安、西安的惊心动魄的经历相比,但却为他晚年的艺术发展预设了伏笔。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仁寿、成都的冯亚珩,就没有延安、西安的石鲁。
从石鲁一生的思想变化和艺术追求看,他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艺术家。他似乎追求着不属于一种文化系统的艺术,也似乎追求着不属于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
从他的一生经历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岁以前,在四川仁寿和成都的学习生活;第二阶段是20岁到30岁,在陕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训练和革命工作;第三阶段是30岁到45岁,在西安从事绘画创作和美术组织工作;第四阶段是45岁以后,在动荡起伏的逆境中,他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命运,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贯穿于四个不同阶段之间的,是两种基本的“信仰”。那就是养成于前20年的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信仰,和养成于陕北十年间的对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改造旧中国的理想的信仰。当这两种信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互相容忍、互相阐发时,他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就比较安宁,就可以以“忘我”的心态从事某种活动;当这两种信仰在某种历史环境中尖锐对立时,他就陷入剧烈的心理矛盾之中,但同时也使他的头脑中闪现出种种在平时难以想象的思想火花。
青少年时期的求学和教学生活,对于他以后的艺术发展设定了难以排除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传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薰染。这种影响不但决定了他后期艺术的走向,使他时时迸发出在“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旁人难以料想的言谈举止。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一阶段,萌发了他追求自由、新鲜、热闹和标新立异的根芽。罗素在论述人类文化的历史阶段时曾指出,他本人是在“一个旧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那是一个比我正在思考着的未来世界更具有偶然性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更多的空隙、更多的例外,那里的人们并不全都被纳入一个确切的模式中……”。石鲁早年就生活在那样一个虽然为他所反感,但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有很多空隙的世界里。那些“偶然性”和“空隙”既是石鲁选择艺术并投奔陕北,接受革命专政的客观条件,也是石鲁在数十年之后在专政环境中酝酿艺术反叛的酵素。
陕北十年,对于石鲁是新的“启蒙”。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石鲁进入陕北后,推动他不断前进的是对一种新的、自由、热烈、充满朝气的生活的向往之情。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政治审查和政治运动锤炼了他,石鲁在这十年中确实有许多变化,但我不能用“成熟”这一类字眼来形容。因为从我的经验中了解到,当人们说某人“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工作上成熟了”,实际是意味着变得圆滑而有城府,同时失去了青年人的敏锐感觉和批判精神。从延安来到西安的石鲁,在精神上是变得“丰厚”和“沉重”了。对于他的绘画创作,这十年间的发展主要在生活的积累和艺术趣味的扩展,而不是技巧、语言的精纯。
30岁以后的1
5年,石鲁在西安度过了尚称安定的生活。他的身分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常常要以美术战线党员领导干部的身分做出决定,发表意见。这当然不符合石鲁个人的性格气质,但又不可推卸,于是出现了各种批评和诸多微词,其根源是处境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而从纯粹的艺术家或者纯粹的党员干部的角度看,石鲁似乎左右为难,而他的那些所谓的“错误”,其实完全可以理解[7]。正是在这1
5年中,石鲁的绘画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即由写实到写意,由反映生活到表现自我,由“新国画”到“文人画”的转变。
1964年前后,石鲁的处境大起大落,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1966年以后,他是在精神病院、监管、斗争批判和潜逃中思索的。但正如一些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一个不公正、受限制、充满着惩罚或压迫的社会环境,对于创造力来说,实际是一种刺激”。心理学家甚至认为,犹太人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天才人物,是由于他们受到疏远,这使他们成为保持怀疑和冷静思考的探索者。其实类似的见解在中国古人那里也早就有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没有1964年以后受挫折和被疏远,石鲁不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当时社会主流思想限囿的思想者,不可能成为一个超越当时流行艺术趣味的真正艺术家。而他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和超越,是与他对生命和人格的了悟同时完成的。
水天中
注
[1]
我早有探访石鲁故乡的念头,但仁寿地处蜀中山乡,往返不便。1993年,应王林邀去成都参加“中国经验”画展和画展研讨会,活动结束后想去仁寿一行。成都的朋友周春芽、何多苓等人替我了解到情况,说是去那里的公路还在整修,暂时无法前往。但天行弟打听到南门外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绕道去仁寿的班车,遂得如愿。
[2]
我回到北京后查资料,得知我是在石鲁出生的那一天到达他出生的地方。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巧合!我愿意将此归因于冥冥之中的天意安排。
[3]
东方艺专于1949年停办。一说1944年合并到中央大学美术系。学校旧址在成都南门外小天竺,如今的华西医大口腔医院附近。但也有说那里原先是公立成都艺专所在地,并不是私立东方艺专旧址。孰是待考。
[4]
当时被称作“老弟”的不仅石鲁一人,来自峨眉山下的张复贤(即张凡夫)也被称作“张老弟”,他与石鲁同龄,后来也去了陕北。全国解放后在东北从事美术工作,以油画创作见长。
[5]
1951年夏,石鲁以西北文联党员领导干部的身分返回四川仁寿,昔日担任东方艺专校长的哥哥在仁寿县当一名教师。石鲁以给西北文联收罗艺术人才的动机,邀冯建吴去西安工作。冯建吴到达西安不久,仁寿县政府的一纸公函将冯氏兄弟告到西安市人民政府:“石鲁返县未经任何组织,即将其胞兄冯建吴带去西北文联工作……冯建吴系仁寿县大地主,农民要求冯建吴返乡退还血债。”当时正是土改运动高潮期,任何一级干部触犯包庇阶级敌人的戒律,都要受严重处分。此函经西北军政委员会批转西北文联,成为石鲁的严重问题。虽然当地乡农会证明冯建吴本人系“自由职业”成分,石鲁仍然做了多次检讨,冯建吴则由专人送回仁寿县,并被处罚款。
[6]
宣侠父原为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地下党员,“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到西安工作,因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策反,被国民党通缉,1938年7与31日夜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石鲁到西安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如石鲁确实见到宣侠父,当为宣侠父生命最后日子的会面。叶坚、石丹合编《石鲁艺术文集》所附年表载石鲁到西安时间为1939年3月,其说似有误。
[7]
就在石鲁在青训班接受政治思想训练的时候,毛泽东曾为安吴青训班作如下指示:“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题词时间为1939年10月。
[8]
如对石鲁在反右派运动中的态度和他与美协老画家的关系,即有不同的评说。但石鲁在建国初期因力荐“民主人士”赵望云出任美协领导,曾在党内受到批评。反右运动中与赵望云划清界线,与此不无联系。
后记:本文初稿写于1994年,2007年6月作了修改调整。文中有关石鲁本人早年生活和求学的史实,主要来自石鲁档案中本人所写的文字材料。石鲁夫人闵力生,美术评论家程征,石鲁的同事和友人程士铭、陈嘉镛、修军等先生都曾给我帮助和指导。在访问石鲁故乡时,得到仁寿县文管所高俊英等同志和我的弟弟水天行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在更大的范围里访问有关专家和前辈,错讹疏漏,恐所难免,希望得到指谬和补充。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冬日的寒凉抵不过大家的热情。 广东美术馆的这个冬天, 因为观众朋友...